2007年8月13日,收錄了8242個遇難者資料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與收錄了2592個幸存者資料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名錄》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數字被轉化為一個個具體的名字。70年后,人們開始從宏闊的歷史敘述中發現那些個體生命的存在。
從關注人的命運的角度去重新觀照那一段歷史,建立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歷史敘述,是為了更深刻地記憶和反思那場悲劇。而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記錄仇恨;牢記歷史,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

高大有 男 60歲 廚師 遇難前家庭住址為中華門外寶塔根105號,遇難時間為1937年12月16日,遇難地點在自己家,遇難方式為被日軍槍殺,加害日軍部隊番號為中島部隊。
周永財 男 被害時年齡為33歲 遇難時間為1937年12月16日,遇難地點為難民區。遇難情形被日軍指為中國軍人抓走后杳無音信。證明人周洪氏,與被害人關系為母子。證明人住址為南京止馬營140號。
黃臘紅 女 8歲 漢族南京人 遇難前家庭住址為中央門外五班村,遇難時間、遺體掩埋時間為1937年12月,遇難地點為中央門外五班村家中,遇難方式為被日軍槍殺,遺體掩埋地點為邁皋橋回子山。
楊得意 男 73歲 籍貫南京農民 被害時住所太平鄉第八保第六甲。遇難時間1937年12月13日。遇難地點為太平鄉第八保第六甲。
……
他們都是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同胞中的一員。長期以來,他們的名字已經湮沒在30萬遇難者的抽象的群體概念中。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去追問他們究竟是誰。而在70年前,那個大屠殺來臨的前夜,他們卻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有自己幸或不幸的人生……
抽象的與具體的

張純如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
這是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對南京大屠殺的一段描述。多年以來,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定格在這種抽象的描述中。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殺中30萬中國人被日寇殺害。他們是誰?他們是怎樣遇害的?卻很少有人追問。遇難者變成了一個數字。
數字化是研究歷史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記住這段慘烈的歷史,光有數字顯然不夠。“受害者不意味著數字,他們是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做了15年館長的朱成山(注:2007年采訪),感到在這種抽象的記憶中,人們與那段歷史越來越遠。
1997年,一本名為《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的書在美國問世,很多西方讀者從這本書中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殺。而許多中國讀者,則從作者獨特的視角和敘述方式中,找回了對那段歷史的情感記憶。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
曾給來南京采訪的張純如作了20多天翻譯的楊夏鳴記得,張純如與我們一直以來的視角非常不同。“她希望采訪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并實地看一下集體屠殺的地點。”
在日軍曾經屠殺了5.7萬人的燕子磯,張純如將攝像機的鏡頭對準了山下破舊的房屋,然后拉到遠處林立的煙囪,接著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遙遠、朦朧的長江對岸。楊夏鳴說:“她仿佛是想再現當年那些試圖渡江的中國士兵那遙不可及的逃亡之路。”在采訪中,張純如不斷向被訪者追問那些生活的細節,甚至早上吃什么東西,平時穿什么鞋,那天的天氣如何?楊夏鳴知道,她是想盡量感受當時南京人的生活細節和氛圍。
正是這種細致入微的采訪,使張純如與那段歷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產生了共鳴。因此,她的敘述才顯得那樣有質感。
其實,在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以前,我們國內已有很多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學術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論述翔實,還獲了獎。但這些文章的敘述語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讀者會去讀。
時隔十年,當楊夏鳴重新翻譯張純如的書時,對書里關于幸存者的敘述也曾有過疑惑。“書中記錄的第一個幸存者唐順山,經歷太有戲劇性了,我曾懷疑張純如敘述中有演繹的成分。”但當重新觀看張純如留在他那里的采訪錄像時,他發現書中的記錄竟與幸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張純如毫無添枝加葉,僅僅用事實就打動了讀者。”
而國內那些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通俗作品,顯得過于情緒化和戲劇化,從而沖淡了史實本身給人的震撼。
史實的力量,是最能打動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記憶猶新的,是他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位于距波蘭首都華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鎮上。1946年波蘭剛剛復國,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確立為國家博物館,并進行原地原貌保存。
奧斯維辛集中營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講解,而是那些壁壘森嚴的圍墻,密布四周的電網,高聳的哨所看臺,是那些曾經結束過110萬人生命的絞刑架、毒氣殺人浴室、焚尸爐……這些原貌保存的場景,使觀者一進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氣場。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展廳里成堆的遇難者穿過的鞋子,用過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猶太人的頭發。這些實物比任何描述,給人心靈的沖擊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除了原地保存的遇難同胞尸骨,更多的還停留在照片加說明的展陳方式上。紀念館所在的江東門地區,就是當年日軍集體屠殺南京百姓的一個“萬人坑”遺址。可在1984年建館的時候,建設者們并沒有刻意尋找遇難者的尸骨,以至于1998年當他們在館內整理草坪時才發現這些遺骨。紀念館研究部主任梁強說:“當時想趕快把館建成,也沒有注意挖掘這么重要的歷史證據。”
遲到50年的追問

2004年,猶太人大屠殺遇難者姓名中央數據庫建成,人們可以從中查到300萬左右遇難者的姓名和個人資料。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哭墻”上僅鐫刻著3000個遇難者的名字。這個巨大的反差刺激著朱成山的神經。
2007年是南京大屠殺70周年紀念,紀念館要進行第三次擴建。新館建成后,展廳面積將從原來的900平方米,擴大到6000平方米。這么大的展廳,展覽什么?怎樣才能幫助人們找回對那段歷史的情感記憶?
朱成山想到了參觀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那個裝滿遇難者檔案盒子的展廳。“那個展廳里,檔案盒從上到下裝滿了整面墻壁。每個可以搜集到的遇難者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檔案盒。盒子上寫著他的名字,里面裝著屬于他的資料,不但有年齡、職業、家庭,甚至還有生前的愛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難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們編成《名錄》,輸入“數據庫”,再制成檔案盒,那將給人們一種全新的了解歷史的方式。
2005年,《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名錄》的編輯工作開始了。
然而,時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談何容易?資料的缺乏是編輯者們遇到的最大困難。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和幸存者的資料,遠比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名字難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多年的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王衛星對記者說,“猶太人進入集中營很多都做了登記,但當時南京的流動人口很多。淞滬會戰時,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難民認為南京是首都,會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鄉下。”
采訪中,南京金陵中學的一位老師向記者證實了這種說法。他說:“那時候,管逃難叫‘跑反’。我們家原本在安徽鄉下,鬼子來的時候聽說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聽說鄉下安全,又跑到鄉下去了。”
這種毫無規律的人口流動,加上連年戰亂,戶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編輯者們不可能根據戶籍查找遇難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幾乎所有研究者在談到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調查時,都惋惜地說,我們動手太晚了。
二戰結束后,猶太人馬上就開始對遇難者資料進行調查,而我們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真正開始。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種種原因,民國史處于歷史研究的禁區,而作為民國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殺,也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紀60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興祖老師曾組織學生進行過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和幸存者尋訪,并且出了一個在校內流通的研究報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歷史條件的限制,現在看來,那次研究的學術價值并不高,它的意義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標志。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篡改教科書事件發生以后,南京學界才重新開始面對這段歷史。
湮沒在證人證言中的名字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
《名錄》的編輯開始以后,編輯者們首先從歷次對幸存者的調查開始尋找線索。
對于幸存者最早的調查始于1945年。抗戰剛剛結束,為了向東京法庭和南京法庭舉證,也為對日索賠作準備,南京國民政府曾面向廣大市民調查抗戰人口和財產損失。當時很多工作人員下到各個街道,向南京市民下發調查表格。同時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說自家的遭遇。
由于這次調查主要是向東京法庭和南京法庭舉證,做得并不全面。而且,當時的報告書稱,“涉及名譽赧然不宣者有之,事過境遷人去樓空者有之,生死不明無從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經極大困難所訪得。”
但這些證人證言中,還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難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證言里,編輯者們看到了高大有遇難的經過: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敵寇入城之際,余因經濟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內家具什件被劫,卒未離去。當日下午,即有日兵數人持槍敲擊屋門,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內蓄米箱內。同屋高大有則因年邁自寬,前往開門,不意日寇進門怒容滿面,向高大有喃喃責問,高因不懂日語,被數人捆綁椅上,以槍擊斃。余蹲箱內見此情形,幾乎昏絕。
而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593—27敵人罪行調查表之七,編輯者們也看到了關于高大有的記錄。于是,這個叫高大有的遇難者被收錄在名錄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編輯者看到了5名被日軍殺害雙親的孤兒悲慘的經歷。呈文這樣寫道:
具呈報人葛家永,現年十九歲,南京人,暫住潤德里二號之一附戶親屬處。緣因民國二十六年,南京淪陷,當時生父葛傳經,年四十一歲,不幸被日敵暴兵殺死,生母張氏、外婆共計三人同歸于盡。難民家前住長樂路小心橋三號,家內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敵搶燒一空,該房屋成為荒地種菜,此損害重大,不堪凄慘,遺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難民當年十一歲,二弟家炎九歲(啞叭),三弟三歲,大妹家貞七歲,二妹家芳五歲,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撫養,救濟生命存世者……
葛傳經以及其妻葛張氏和其丈母,也被收錄在《遇難者名錄》中。
就這樣,編輯者們一點一滴地從這些60年前的資料中,積累著遇難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名錄》中更多的資料來源于新中國成立后做的兩次調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過兩次大規模的大屠殺幸存者尋訪活動。這兩次尋訪工作,可謂是搶救性的。但是,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這兩次調查的方式,并不讓人滿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開展了一次為期五個月的幸存者調查。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還記得那次調查的范圍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對南京10個城近郊區55歲以上的人都進行了調查。”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由南京市各區縣機關、文化館、街道的工作人員組成,也包括部分學校的師生。當時發現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證言更是觸目驚心。
幸存者唐廣普描述了他從日軍集體屠殺中死里逃生的經歷。當時,15歲的唐廣普是中央軍的一名士兵。日軍攻入到南京后,他與兩萬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軍趕到上元門大洼子江灘。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條,開始綁人,從早上四點鐘一直綁到下午四點。然后,日本兵讓他們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點,日本兵開始屠殺了。他回憶:“機槍一響,我就躺倒在地。20分鐘后,機槍停了。我右肩頭被打傷也沒有知覺,死尸堆積在我身上,特別重。5分鐘后,機槍又開始掃射。過了一陣子,日軍上來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樹上,用汽油一澆就燒起來了。”這時,他從死人堆里掙扎著爬出來。而那次大屠殺,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諸。
調查中,雖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備,但是從專業角度看,孫宅巍認為那些口述記錄做得非常業余。“除了這些基本信息,還應該問到受難者當時的感受,后來的生活,以及災難對其日后生活的影響等情況。但是,這次調查并沒有涉及。”孫宅巍認為,這主要是緣于調查者水平的問題,參加調查的人大多數缺乏相關的歷史知識和采訪技巧。幸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時隔多年,沒有采訪者的良好采訪技巧是很難描述出生動場景的。
調查者的業余性,也是后來幾次尋訪中最大的問題。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與日本友好團體合作,組織南京11個區縣的14000多名高中生對幸存者進行尋訪。4個學生作為一個小組,對南京70歲以上老人進行地毯式尋訪。活動之前,教育局給每個小組配備了錄音機、照相機,甚至還給了沖膠卷的經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特意組織教師代表進行培訓,告訴他們如何提問,如何筆錄。
但調查的結果卻令他們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強回憶,那些中學生的報告五成以上非常粗糙,對一件事的敘述不完整,時空觀念混亂,有的連幸存者的年齡、受害地點、受害方式都沒有,“只是含糊地說,死了。調查中幾個重要的時間、地點信息不詳,就無法使用。”
編輯《名錄》時,這些調查表著實讓編輯者頭疼。顏玉凡記得,有的調查表字跡非常潦草,她經常要拿著表請館里的同事幫助辨認。“有時候,前文本來是‘他’,不知道為什么就變成‘她’了。記錄中還有很多宏觀的描述,像‘我們家門前堆滿了尸體’,但有效信息很少。”
結果回來的2460份調查表,最終只確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
十年之后,記者試圖尋找那些曾經參與過調查的老師和學生。金陵中學學生工作處的劉老師在厚厚的學生社會實踐報告中為記者翻到了一篇當年高三(二)班學生對一位幸存者的訪問記錄。記錄中老人向學生描述了他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記錄日軍暴行的照片。但當記者請劉老師聯系這個班的老師和學生時,卻異常艱難。校長、政教處老師、班主任全都不記得十年前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活動。那些學生更是杳如黃鶴。最后,對這個活動還有些許記憶的劉老師自言自語道:“當年記者采訪,媒體報道,多么轟轟烈烈的一件事啊!怎么都不記得了……”
缺乏系統的訓練和組織,直接影響到調查的結果。對此,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開始進行幸存者調查的張連紅深有體會。他說,記錄口述歷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學問題,對采訪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訪者具備相關的歷史知識,需要對被訪者有一些了解,要做問題設置。“對提問要進行細化,比如被訪者的年齡,職業,家庭情況,戰爭來了為什么沒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問題。這樣,一個豐滿、富有個性的人才能勾勒出來。”
與被訪者之間的情感聯系對于訪談也非常重要。令張連紅至今念念不忘的一個老奶奶,12歲在孝陵衛砍柴時被日本兵強暴了。以后的歲月里,她曾兩次嫁人,因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敗了。她看到張連紅經常陪一個鄰居老太太聊天,覺得他人不錯,才對他開口。而此前,她沒對任何人說過,包括她的兩任前夫。張連紅記得那個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凈,“你無法想象一個80歲的老人,家里比年輕人還干凈。由于日本兵的強暴,在她心中對臟特別敏感。我采訪她的時候,她一個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關門。”
這種細節化的東西,非專業的采訪者是很難挖掘出來的。而遺憾的是,由于教學、研究等工作壓力,現在張連紅已經很少做幸存者調查了。
1984年調查出來的1756名幸存者,現在也只剩下了400人(該數字截至2007年發稿時。至2025年12月13日,幸存者僅余24人)。
私人日記中的記憶

約翰拉貝。
《名錄》的另一個資料來源是近年來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記。
1937年,大屠殺來臨之際,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國人沒有跟隨他們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來成立了安全區,并挽救了25萬南京市民的生命。他們中的許多人為這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記憶。長期以來,這些私人日記一直沒有公諸于世。
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個寄自德國柏林的包裹,打開一看,竟是長達87頁的“拉貝致希特勒的報告書”和“拉貝先生簡歷”。
德國商人約翰?拉貝是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稱為“活菩薩”。而戰后,他卻沒有像他在安全區的同事那樣,出現在東京審判的證人席上,關于他的信息也沒有再出現。
但朱成山相信拉貝一定留下了對于南京大屠殺的回憶。1995年當張純如來到紀念館尋找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時,朱成山建議她到德國尋訪拉貝的足跡。
“當時,我只是給她提供一些線索,并沒料到她真的會去查找。”更沒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貝先生的外甥女賴因哈特夫人,并且發現了塵封59年的《拉貝日記》。
賴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據張純如留給她的地址,給朱成山寄來了拉貝的資料。朱成山趕緊請人翻譯,并對資料的內容和真實性做了研究和考證。在這過程中,賴因哈特夫人受到紐約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陳憲中、邵子平等邀請,于1996年12月13日,在美國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貝日記》。
后來,紀念館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幫助下,從拉貝親屬那里征集了2460頁的《拉貝日記》和拉貝收藏的128張南京大屠殺歷史照片復制件,他當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箋、木箱、煙袋,以及拉貝夫婦的墓碑等一批文物。
《拉貝日記》里詳細記錄了南京城破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個細節讓后來讀過此書的顏玉凡潸然淚下:“有一次,拉貝要回德國。得知這個消息后,安全區里的婦女們給拉貝跪下,求他不要走。我能體會到那些難民當時的無助,拉貝在他們心中簡直就像救星一樣。”事實也確實如此。大屠殺期間,拉貝不但收留了無數市民,還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闖進安全區的日本兵趕出去。
在1938年2月2日的日記中,拉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寫的南京事態報告,開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為秦王氏的22歲少婦,1938年1月23日被日軍從安全區難民收容所拉出,此后杳無音信。
還有一位60多歲的老嫗,在三牌樓火車站被日軍強奸達十余次。但文中沒有寫明她的資料。面對這些無名受害者,編輯者們也只能放棄了。
除了拉貝,當年安全區的明妮?魏特琳、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塵封在海外的檔案
即便加上后來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記,中國大陸所有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萬字,歷史研究需要史實作為支撐。于是,國內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2000年,在南京大學中國民國史研究中心張憲文教授組織下,一個聯合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社科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單位,六十余位教授、學者組成的團隊,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海外搜集史料的活動。
2003年曾赴日本東京搜集史料的王衛星,提起在日本的經歷,仍感慨良多。
從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東機場乘飛機。因為航班是早上10時起飛,一般人會選擇頭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實實上飛機。但為了節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費,王衛星選擇乘夜里12時的火車到上海。由于是過路車,根本沒有座位,他只能提著行李一路站到上海。
在東京查資料的兩個月,王衛星一天也沒有休息過。日本防衛廳的軍方檔案復印手續非常繁瑣,要填寫申請書,留下在日本的通訊地址。為了保護檔案,不能直接復印,需要照相、制版,然后才能復制。而這個過程,至少要三個月以上。
王衛星決定抄寫。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個小時以上。“我全是原文抄錄,即便是原文中的錯字,也原樣抄回來。回來以后再翻譯。”
東京的物價很高,為了節省開支,他吃了兩個月的面條。“張老師籌點錢不容易,我們都想節省一點兒,把錢盡量用在收集資料上。”
結束在東京的工作,乘機返回中國時,王衛星帶回的資料有20公斤,為此還補了飛機貨票。
歷時5年,學者們先后赴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和中國臺灣搜集史料,共搜集、整理、翻譯了1500萬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
這些封存在海外的檔案,為《名錄》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楊夏鳴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收集了東京審判中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全部資料。這些資料,60年來一直塵封在美國,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現在國人面前。
里面大量的證人證言,不但揭露了日軍的暴行,還為編輯者們提供了很多遇難者的信息。
取舍之間

侵華日軍進入南京城。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日益豐富起來,那些曾經遮蔽在抽象數字和形容詞后面真實的歷史漸漸顯露。雖然以往的資料都不是以人為記述對象的,但《名錄》的編輯者們認為,把那些淹沒在史料中的名字拎出來,不是特別困難的事。
作為朱成山的研究生,顏玉凡從一開始便參加了《名錄》的編輯。她記得查的第一本書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志日》。那本書按日期把每天發生在南京的暴行記錄下來,收錄起來并不困難。但隨著翻閱史料的增加,顏玉凡感到越來越難。
由于歷次做調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幸存者和遇難者的信息也不全。有的人沒有遇難的地點和方式,有的人遇難時間不明確,有的人沒有遇難時的年齡,有的人甚至沒有正經名字。“什么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張鐵匠,只要有一個指代,我們都收錄了。名字只是個代號,就算有一個外號也能證明這個人曾經存在過。”但幸存者敘述中,被日軍用鐵絲穿過鎖骨掛在樹上的七八個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婦,被成千上萬集體屠殺的繳械士兵,卻只能放棄了。“畢竟,我們是名錄,必須要有一個起碼的稱呼。”
更令顏玉凡他們為難的是,在歷次調查留下的材料中,受害者資料常有互相矛盾之處。
“有的名字,同音不同字,卻是一個人。”
編輯者張亮記得,在1946年調查中,有一位叫周永才的男子,1937年12月在大方巷10號被日軍擄走后,杳無音信。而1945年他母親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他的名字卻變成了周永財。“這顯然是一個人。只是因為調查人員沒有核實名字才記錯了。”
還有很多人名,同音同字卻不是一個人。編輯者楊曉宇記得,那時候婦女很多叫秀英,名錄里光幸存者就有不下十個張秀英。此外,舊時代婦女沒有正經名字,結了婚以后都從夫姓,“什么王王氏、王李氏重復的就更多了。”他們往往根據遇難者的年齡來判斷是否是同一個人。
顏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個“戴呆子”。她感覺這5個戴呆子其實是一個人,但不同的記錄里,他們遇害的時間不一樣,遇害的地點也不一樣,遇害的方式還不一樣。“但我發現這些錯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聯系。有的資料寫他遇難時在估衣廊133號,原住址是韓家巷6號。有的資料寫他遇難的地點是韓家巷6號。這可能是調查時發生了混淆。有的資料寫他在日本兵強奸一個婦女時闖進,被日本兵槍殺,有的資料就直接寫槍殺。”種種跡象表明,這5個人名,其實是一個人。
如果遇到實在難以決斷的時候,顏玉凡就去請教館長或者標上注釋,她從不敢擅自刪掉一個人名。“因為我覺得這個責任太重大了,我承擔不起。”
在取舍時,最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錄》之外的生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東京法庭認定南京大屠殺的時間范圍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這六周,空間范圍則是南京特別行政區劃內11個區。“不是說,這之外就沒有屠殺,只是,這六周是屠殺最慘烈的時候。”
但這樣的劃分,使相當一批遇難者和幸存者被排除在《名錄》外。顏玉凡記得,一份記錄中,南京郊區有一個村因為拒絕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殺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幾個人。但這個屠殺卻發生在1938年4月間。由于時間不符,只能從《名錄》中刪除了。
這種抉擇讓顏玉凡非常難過,“很多在那六周被殺害的人,想找到他們的名字都沒有,而這些有名有姓的人,卻不能收錄進去。”
可是,作為一名歷史工作者,理性永遠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說:“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南京大屠殺的時間地點是有明確概念的。我們要對歷史負責,真實地記錄歷史。如果任憑感情驅使,擴大《名錄》的范圍,那么日本右翼勢力又會找到否認這段歷史的口實。”
第一批《名錄》出版了,數據庫中原有的9600多個遇難者名字,最終只收錄了8242個。
那些逝去的面孔

幸存者素描
《名錄》編輯將近尾聲時,朱成山覺得只有名字和簡單資料,那些遇難者還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有很多遇難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個個笑靨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殺來臨時,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無情地摧毀了。“如果我們能找到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形象,那對于今人來說,將是極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國,有照片的人寥寥無幾。“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錢人。當時,有些積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殺中遇難的大多是社會最底層的平民。他們怎么可能有照片呢?”
況且,經歷70年,那些老照片能保存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記者從一份檔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親給南京國民政府的呈文后面,曾經附上兩張他遇難兒子的照片。60年后,這份檔案上標明,照片已遺失。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曾面向社會征集過遇難者照片,但幾年過去了,只收集到二十幾張照片,有的還是畫像。這與三十萬的死難者人數太不相稱了。
怎樣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場買東西的時候,看到商場里有人正在用電腦給顧客畫像。這一幕觸動了他的神經。“可不可以采用電腦畫像的方式來給遇難者畫像呢?”回到館里,他馬上讓工作人員尋找電腦畫像的設備。幾經尋找,他們終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偵查的電腦畫像軟件。軟件中存著幾百張人的五官類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這些五官拼起來,遇難者的形象不就出來了嗎?這個發現,讓他們非常激動。
軟件買來后,紀念館工作人員燕龍溪和司機小孫開著車,帶著設備開始了對幸存者的走訪。時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還能否記得當年親人的相貌,燕龍溪沒有把握。走訪了幾家之后,他發現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繪出那些逝去的臉。那段慘痛的經歷,給他們的印象太深了。
畫像工作進行了一段時間后,燕龍溪發現一個問題。由于這套系統原來是為公安部門作刑事偵查用的,所以圖譜中沒有老人和小孩的資料。怎么辦?他們只好求助于軟件開發商。
為此,兩個山西工程師特意趕到南京來為他們改進系統。圖譜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龍溪又拿著照相機,到幼兒園和小學去給孩子拍照。“當時也不敢告訴人家是為了給遇難者畫遺像用的,怕人家忌諱嘛!只能含糊地說,留作素材。”
一輛車,兩個人。一年間,燕龍溪他們在南京跑了將近10萬公里,走訪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難者的遺像畫出來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親朋的形象,非常激動。他們:“像!像!就是他……”
有的幸存者知道這個消息,全家扶老攜幼到館里來畫像。給燕龍溪印象最深的是一個90多歲的老爺子,當年是國民黨守軍。去年夏天,他自己騎了40分鐘自行車來到館里畫像。臨走時,燕龍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爺子執意要自己騎車回家。
雖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對電腦畫像很認可。但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并不滿意,梁強說:“電腦畫像畢竟是拼起來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個人像不像,有時候就是一個神態。”電腦拼出來的人,顯然沒有表情。
為了能畫出更生動的遺像,紀念館聯系到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張玉彪,請他來為遇難者畫像。張玉彪爽快地答應了。
幾個月間,張玉彪跟著燕龍溪走訪了30多個幸存者。畫像前,張玉彪會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與遇難者找到聯系。那些慘烈的歷史,深深觸動了他。
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強。
1937年,常志強只有9歲。大屠殺來臨時,他與父母、姐姐和四個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瘋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現,瞬時殺害了他的6個親人。他的母親在臨死之前,還堅持著給他年僅兩歲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強看到母親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趕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還念叨著:“媽媽,我給你捂著,我給你捂著……”但常志強留不住媽媽的生命,他兩歲的小弟弟,最終也被活活凍死了。說到此處,80歲的老人已經老淚縱橫。
記者在南京采訪時,記錄了常志強遭遇的影片《南京》還在南京放映。看過影片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常志強也接受了各地記者采訪。反復地回憶顯然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傷害。記者見到他時,他正戴著檢測心臟的儀器,坐在醫院的病床上。
記者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慘痛的歷史。當老人看到記者從張玉彪那里帶來的他小弟弟的畫像時,非常高興,點著頭說:“像,真像!這就是小發。我這么可愛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對于接觸到大量真實的細節和場景的編輯者來說,不帶感情地記錄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的。
顏玉凡對此深有體會。剛剛編輯《名錄》的時候,遇難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對她來說只是個符號。但隨著資料的豐富,那些遇難者和幸存者的形象漸漸豐滿起來。而她也深深地被這段歷史所震撼。《名錄》編輯過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時候,我經常失眠。即便睡著了,也會夢到那些撲面而來的名字。”編輯即將完成時,她不得不離開這項工作,回家療養。
朱成山記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學生顏玉凡的信息,信息中顏玉凡說她看了老師在電視臺做的節目,哭了。她問老師,這么多年來接觸這些慘烈的歷史,是怎么熬過來的?
朱成山這樣回復她,“帶著感情去研究歷史是對的,但不要帶著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時間為這段歷史吶喊,現在我覺得光吶喊不夠,還要有理性。”
采訪中,幾乎所有學者都對記者強調要“理性地研究”這段歷史。
王衛星說,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記錄仇恨,而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讓人類從悲劇中吸取教訓。大屠殺不是哪個民族的悲劇,而是全人類的悲劇,人性的悲劇。以這樣的情懷進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不會增長仇恨,只能讓人們以史為鑒,更加珍惜和平。
他說:“很多人問我,為什么南京大屠殺不像納粹屠殺猶太人那樣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覺得,某種程度跟我們的敘述方式有關。張純如站在人性的高度進行敘述,人道,是人類共同的語言。”
2005年,在南京召開的納粹屠猶與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位以色列學者說:“我希望,當人類再有災難發生時,我們不再成為受害者,不再成為旁觀者,更不成為加害者。”
這,也許就是我們強調牢記歷史的意義所在。
原標題:讓昨天告訴明天——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和幸存者名錄采集紀實
原載于《北京日報》2007年9月11日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微信公眾號
如遇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相關文章刊發之日起30日內與本網聯系。版權侵權聯系電話: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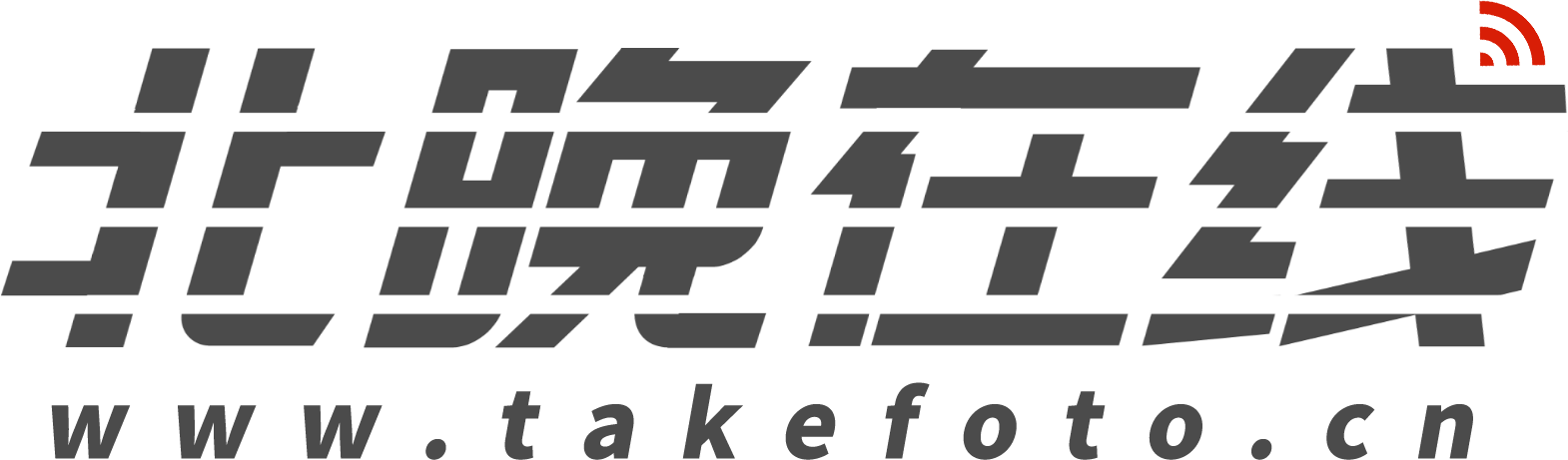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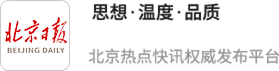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未登錄
全部評論
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