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一天,電影《南京照相館》黑白特別紀念版,將在南京、北京等五城的部分影院限定放映。
電影的導演、編劇申奧在文章中寫道:“當年,不只是一個國家的人、一個膠卷、一本底片,讓這一歷史真相不被掩蓋和遺忘。”
正如導演所說,除了主角的原型羅瑾和吳旋,影片中的很多角色都有原型。比如,影片中有一幕是日軍去金陵女子學校抓人,一位美國女醫生因阻止日軍的暴行,被日軍直接扇倒在地。這位女醫生的原型就是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彼時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南京淪陷期間,學校設立的婦女兒童難民收容所收容了一萬多名婦女和兒童。那些血流成河的日子里,魏特琳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留下了五十余萬字的《魏特琳日記》。那些文字里充滿了道義和悲憫,記錄了一段血淋淋的歷史。
“無論如何也不離寧”

魏特琳(左)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玫瑰園留影。
“我認為我不能離開……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1937年8月27日 《魏特琳日記》
魏特琳的第一篇日記寫于“八一三事變”爆發的前一天。日記中記錄,學校決定把開學日期推遲到1937年9月20日。顯然,這是受到一個月前“七七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影響。不過,戰爭似乎還只是在遙遠的中國北方進行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甚至還準備在第二周安排在上海進行入學考試。可8月13日,上海就覆蓋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了。
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教授介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學,創辦于1915年,是中國第一所教會女子大學。當時的校長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留美女博士吳貽芳。魏特琳是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魏特琳還有一個身份是傳教士。她1912年就來到了中國,先是在合肥創建了一座女子中學,1919年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教。張連紅說,外國傳教士大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并且和他們的宗教組織、朋友保持著密切的通信往來,這使他們的日記、信件成了保存完備的歷史資料。
魏特琳的文字中,沒有透露寫日記的初衷是不是專為記錄這場戰爭,但日記卻是從這場戰爭開始的。
張連紅告訴記者,魏特琳在1937年8月11日給朋友的信件中,也有一部分類似日記的回顧,最早的記錄始于1937年6月。那時,她正在青島享受著暑假。在那里,她得到了“七七事變”的消息。對她來說,戰爭爆發得很是突然。信中的描述是:“7月7日,一個日本兵失蹤后,在北平南面數英里的地方出現了麻煩……自那以后戰爭擴大了……”
魏特琳在信中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作類比,對中日戰爭做了這樣的判斷:“1914年在薩拉熱窩有兩個人被打死,歐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殺死1100萬人。”
她還是低估了日本侵略者的殘忍。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付出了3000萬條生命的代價。就在她生活的南京,數月之后,僅僅6周內就被屠殺了30萬人。
上海“八一三事變”后,日軍從8月15日開始了對南京的每日空襲。政府命令市民將屋頂、墻壁粉刷成灰色或黑色,以防空襲,并在地下開挖防空洞。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心理學老師的張小松回憶:“城市好像在舉行一場盛大的葬禮。”
日本叫囂著“三個月滅亡中國”,傾盡全力進攻。上海的戰事慘烈成了絞肉機。中國軍隊以每天拼光一個師的代價,進行著殊死抵抗。相隔不遠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如累卵。
國民政府從淞滬會戰開始就逐步撤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部分師生也都撤退到后方,自愿留下來的4名教師和11名職員組成了留守委員會。魏特琳任代理校長。
11月17日,宋美齡將一架陪伴自己多年的鋼琴送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這位第一夫人很快也要離開南京了。11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發表《遷都重慶宣言》。
上海在拼死抵抗了3個月后陷落,日軍的兵鋒直指南京,槍炮聲越來越近。
美國大使館早就一次次召集滯留南京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后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但魏特琳每一次都予以拒絕。她向美國大使館借來一面3米多長的美國國旗,平鋪在學校中央的草地上,以保護學校免遭日本飛機轟炸。幾天后,魏特琳覺得這面美國國旗太小,又讓工人買布制作了一幅10米長的美國國旗。
美國國旗顯然不能抵擋炸彈。南京遭遇了長達4個月的瘋狂轟炸,魏特琳曾在日記中描述被轟炸后的南京:盡管中央醫院和衛生署屋頂漆了一個很大的紅十字標志,但仍有16枚炸彈被故意地投在院落里……學院網球場東面禮堂的西墻倒塌,所有的窗戶都破碎了。其余有軍事、政治意義的轟炸目標更不待言。
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勸不走魏特琳,就給她送來了幾大捆繩子,半是警告半是幫助:“一旦長江上的美國軍艦載著大使館的官員們離開,中國軍隊關閉城門后,你們唯一的逃生希望就是用繩子結繩梯翻越城墻了。”
12月1日,完成了軍事部署的日軍當局下令:“攻占南京。”古城金陵,陷入血火。
美國大使館在12月3日最后一次通知魏特琳,她有3個選擇:即刻就走;最后時刻搭乘最后一艘美國軍艦撤離;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走。
她選擇了第三項,并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文件證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五次拒絕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要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國使館,指出各國使館這樣撤出是很不明智的。
在南京,魏特琳試圖保護的并不只是這所美國教會學校。
南京安全區

學校的教室成了難民的棲身之地。
這是一個凄涼的暮秋日子,悲切的秋風整夜都在哀號。對我們這些在南京的人來說,世界仿佛成了悲傷和被人遺棄的地方。
——1937年11月19日《魏特琳日記》
此時,自愿留在南京的,除魏特琳,還有20多位歐美人,多是傳教士、教授、醫生或商人。他們希望在南京設立一個安全區,為平民提供避難場所。
在南京建立安全區的決定可以說是這些歐美人士一種自發的決定和行為。此前的淞滬會戰中,法國神甫雅坎諾(中文名饒家駒)在上海南市建立的安全區救助了20萬中國難民。以此為例,留守在南京的歐美人士也計劃建立一個安全區,在注定要遭受涂炭的南京提供一個避難場所。
7位美國人、3位德國人、4位英國人和1位丹麥人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12月1日成立。委員會主席就是后來被中國人無數次感念的約翰·拉貝,魏特琳也是成員之一。
早在南京淪陷前一個月,魏特琳就致信美國駐華大使館,建議在南京城內設立安全區以收容難民。她在信中說:“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來說,金陵女子大學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南京安全區東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漢中路,北面到山西路與中山北路一帶,占地約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國使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機構都在其中。安全區內非軍事化,設立26個難民收容所。
安全區的中立和不受戰爭侵害的地位,必須要交戰雙方認可才能實現。張連紅告訴記者,安全區雖冠以“國際”的頭銜,但實質僅為涉及幾國公民的個人行為,并非國際政治學意義上的“國際組織”,因而對主權國家不具約束力,安全區的安全與否,完全取決于日本軍事當局的意愿。只要日本軍方不合作,安全區注定不安全。
南京國民政府倒是對安全區給予全力支持。根據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的記載,當時的南京市長馬超俊把安全區的行政責任交給了國際委員會,還提供了450名警察、4萬擔米糧和面粉,及8萬元現款。安全區內原本有中國軍隊的高射炮陣地,很快被撤走。
在通過美國大使館和日本當局進行了交涉之后,12月1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收到日方通知:只要與日方必要的軍事措施不相沖突,努力尊重此區域的中立。
這樣的口頭承諾完全沒有實際意義。張連紅說,實際上,日本一直拒絕承認南京安全區。日軍占領南京后,并未遵守與國際委員會的約定,經常強行闖入安全區,劫掠財物、奸淫婦女,大肆抓捕青壯年并予殺害。國際委員會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館及日軍當局提出抗議,但是日軍暴行并未收斂。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后的一周,魏特琳和教工們把大部分家具從中央樓、科學樓、音樂樓和實驗樓里清理出來,也清理了宿舍,準備安置難民。魏特琳還專門安排了幾個少年,為難民帶路。
12月12日晚的南京,沒有電燈,沒有水。魏特琳和衣躺在床上,聽著重炮轟擊著城門,和城內激烈的槍聲,一夜未眠。此時的南京,不通電話和電報,沒有報紙,沒有廣播,成了與世隔絕的死城。
次日凌晨,南京淪陷。據歷史學家統計,當時的南京城,約有50萬平民和9萬中國軍隊。入城日軍則有5萬。
這一天,魏特琳5時起床,去校門口探看究竟。
南京的大街上,商鋪緊閉,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一些老百姓家里掛出了日本國旗,以求平安。
安全區的街上則擠滿了人。
魏特琳站在校門口,看著數以千計的難民涌入校園,臉上都帶著驚恐的神情。目睹那些裝扮成男人和老太婆、哭泣著跪在門前的婦女,魏特琳立即讓她們都進入校園,并竭盡全力保護她們。
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魏特琳寫道:“迄今為止,學校的員工及建筑物均安然無恙,但我們對今后幾天的命運毫無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極點。”
累累獸行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里找到。
——1937年12月16日《魏特琳日記》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幾乎是同時,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開始,整個城市一片血海。30萬中國平民和戰俘在南京淪陷后的六周內慘遭屠戮。
日軍進入南京后,除了野蠻屠殺、搶掠之外,最普遍的罪行就是對婦女的性暴行。究竟有多少婦女在這場劫難中遭到侵略者的蹂躪?據當時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估計,發生在南京的日軍對婦女的強奸案起碼有2萬起。許多性暴行令人發指,“一位48歲的婦女被強奸了18-19次,她的76歲的母親被強奸了2次”。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兒童的難民所,南京淪陷后,有大批女難民涌入。原本估計將有2700多名難民到這里避難,但由于日軍瘋狂地強奸、屠殺,驚恐萬分的女人和孩子們紛紛涌入,最多時超過1萬人。
實際上,安全區對婦女來說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別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因為聚集著這么多年輕女性,更被日軍視為獵取獵物的主要目標。
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抓人,強奸婦女,搶劫錢財。他們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翻越圍墻進校園,還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進來的,在無燈光的大樓里,樓上樓下亂搜一氣。
16日一早,一百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國士兵為由,闖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架起六挺機關槍。他們備有一把斧頭,遇到打不開的門就強行劈開。魏特琳想起樓上地理系辦公室還放著數百件婦救會為傷兵做的棉衣,急中生智將他們帶到別的地方。凡是帶有中國軍隊痕跡的物品,都可能帶來殺身之禍。天黑后,這批原本打算留下來給難民御寒的棉衣被悄悄燒掉。
這一天,也即日軍進城第4天,拉貝在其日記中寫道:昨夜里1000多名姑娘被強奸,僅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強奸。一位美國人說:安全區變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17日,一名日軍中士帶著一隊日本兵開著卡車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以搜查中國士兵為借口,將魏特琳和另外三名外籍人士控制在校門外,強迫中國職工集體跪在門口,一個日本兵打了魏特琳耳光,其余的士兵趁機跑進大樓挑選并強行帶走12名年輕姑娘。
張連紅在1999年曾和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東史郎會面。東史郎告訴他,當時他們這些駐扎在南京的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里收容了許多年輕姑娘。日軍是三五成群,不分白天夜晚侵擾,有時就在“金女大”校園直接施暴。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趁著夜色翻越校園圍墻,在黑暗中抓走婦女。日本士兵中,對這種行為稱之為“摸彩”。
張連紅還訪談過很多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所的幸存者。門房杜師傅的妻子趙政蓮回憶,她當時睡在門房里,經常能聽到卡車開進來的聲音。當時,一聽到汽車聲,女難民們便用泥或鍋灰擦臉,但日本兵卻帶有濕手巾,一個一個去擦難民的臉,看到年輕漂亮的就用白被單一裹,然后送到卡車上去。
在那些孤立無援、極度恐懼的中國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
對于學院中豎立的中立區標志,日本兵根本不當回事。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孺,更是他們肆意凌辱、屠殺的目標。只有歐美人相貌的魏特琳出現并大聲叱喝,他們才會收斂。
魏特琳每天奔波在學校的各處,將哭叫著的婦女從日本兵手里奪回來。人們聽見她隔老遠就怒氣沖沖地大喊:這是美國學校!
拉貝則在日記中這樣描述,魏特琳“像抱窩的老母雞帶小雞那樣保護著她們。當日本士兵的暴行變本加厲的時候,我親眼看見她走在100多名女難民隊伍的前列,帶著她們走向大學難民收容所”。
對于暴行,魏特琳沒有表現出一絲畏懼,但最讓她心痛的,卻是這些中國女人的遭遇:“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她的日記,被憤怒和痛苦填滿了:“假如日本婦女們知道她們的士兵——她們的丈夫和兒子所加諸中國人的野蠻和殘酷,我不知道她們該作如何的想法。”
血色平安夜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工作人員合影。(左四為魏特琳,左五為程瑞芳)
大火仍映照著南面與東面的天空……我不想看南京,因為我肯定它已經是一片廢墟。
——1937年12月24日《魏特琳日記》
1937年12月24日,圣誕節前一天,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日軍的燒殺搶掠仍在持續,南京城南與城東火光沖天。
這一晚,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再過一天就是圣誕節了。我被叫到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后,我們允許他們挑選……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于找到了21人。”
這幾行文字,在2005年被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看到,發酵成小說《金陵十三釵》: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學生充當日軍慰安婦。
張連紅認為,妓女主動獻身的故事是作家演繹出來的,是文藝作品中的情節。歷史資料中,可能找不到這樣的情節來映射極端情況下人性的升華,但是,日軍人性喪盡的惡行記錄,卻比比皆是。
單是日軍在平安夜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挑選“妓女”一事,就有數位見證人做出了記載。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舍監。在救助難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也用日記逐日記下日軍的暴行。程瑞芳日記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一部由中國人以日記體記錄下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暴行的文字材料,因此彌足珍貴。
相對于拉貝和魏特琳的日記,程瑞芳日記文字零散、簡略,但滿紙皆是死亡、殺戮、暴行,難以遏制的憤怒和咒罵流溢筆端。
“這些(日本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簡直沒有人道。”
“憲兵還是將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生,不管什么地方。”
12月24日,程瑞芳的日記里也記錄了這一天發生的事:“今日有參謀官帶幾個中國人來此找妓女,若是有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家女子受害,這些話也是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讓他們找,內中有幾個中國人認識妓女的。”
著有《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華裔女作家張純如,也在書中記錄了這件事。她認為“魏特琳在與日本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有時也犯錯。就像拉貝曾被日本人欺騙而將一些中國人交出去,結果這些人被處死一樣,魏特琳也曾將一些無辜的婦女交到日本士兵手中。”
程瑞芳的日記似乎可以印證張純如的推測:“也許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話——一旦慰安所里有了這些妓女,他們將停止騷擾難民營里的未婚女子和良家婦女。”
這當然是日本軍人的鬼話。
張連紅1999年走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時,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憶了事情經過。當年14歲的屈慎行是南京下關區安樂村村民,當時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里避難。
“有二十幾位維持會人員來金女大,尋找以前做過妓女和做過招待的婦女,他們在學校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尋找,目的是想把她們拖到外面去參加組織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卡車拉著走的。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車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屈慎行告訴張連紅。
這些被挑走的“妓女”,顯然并沒有起到日軍所說的“作用”。魏特琳的日記顯示,無論在安全區還是在其他地區,還是不斷有女人被強奸,就在新年前幾天,有27名婦女在“圣經師資培訓學校”里被強奸。
那一年,魏特琳51歲,程瑞芳已經62歲,許多天她們和衣而眠,經常坐到12點鐘才睡。她們守護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1萬多名婦孺,卻左支右絀,防不勝防。
“良民證”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的工作人員和學生。
約兩百名年輕婦女來磕頭,懇求我讓她們留下來,而我們并沒有強迫她們回家的想法。后來,當米爾斯走時,她們在他的汽車前哭泣和磕頭。可憐的姑娘們!
——1938年2月4日《魏特琳日記》
1938年1月1日,日軍在南京成立了偽自治委員會,命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所有行政權和錢款、米糧移交給偽自治委員會。1月28日,日本人下令關閉難民收容所,限定難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同時,日軍規定,所有中國市民必須登記領取“良民證”,否則便認作是中國便衣隊,格殺勿論。這種殘酷的殖民統治,更包藏著有組織屠殺的禍心。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被設立了一個登記點。登記對象并不限于這里收容的婦孺,而是包括了周邊安全區內的大量中國平民。
男子的登記首先開始。魏特琳注意到,前來登記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殘疾人,“因為大多數年輕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殺。”
日軍通過翻譯聲稱:“如果是中國士兵,應該自首,那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他們所說的“中國士兵”,不但是已經放下武器的現役軍人,曾經當過兵的也算在內。有人“承認”了,被拉到校園的東北角集中,然后又被日軍帶走。即便是那些從未當過兵的男性,也被一一檢查了手掌。日軍從手掌的粗糙程度來判斷他們是否有從軍經歷。那些裁縫、小販、手工業者,也被歸納到“中國士兵”中。
幾天后,這些人中的一個又回到了安全區。他告訴魏特琳,當天一起被帶走的二三百人都被殺死了,他僥幸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
隨后對女性的登記充滿了羞辱。魏特琳觀察到,日本士兵像趕牲口那樣將婦女們趕來趕去,并從中得到極大樂趣。有時還會將印記蓋在她們的臉上。“日本人還強迫這些婦女為日本記者和攝影師露出微笑和高興的樣子。”
魏特琳甚至覺得,日本人要對中國婦女登記,只不過是為了挑選最漂亮的婦女作為強奸對象。有20名姑娘因為燙著卷發,穿著高檔就被單獨列隊。幸而,日軍企圖將她們帶走的當口,安全區內的外國人士和她們的親屬出面攔阻了下來。
“良民證”登記之后,日軍試圖取締安全區。一些人按照他們的要求離開了,但很快又逃了回來。盡管安全區內也不能保證安全,在已經是人間地獄的南京城內,這里卻是唯一能夠提供庇護的地方。
日軍規定的最后期限到來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還有4千多難民,多數是年輕姑娘。許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躪,第二天又回來。每天仍有女難民來學校,魏特琳頂著壓力收容她們。
2月4日這一天,一隊日本軍人來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要求所有的婦女和孩子一律離開。魏特琳堅決地站立在他們和難民中間。她告訴日軍,這些婦女的家都被焚毀了,無家可歸,不可能離開收容所。
日軍并沒有向魏特琳發難,悻悻而回。那位跟隨日軍而來的中國翻譯,悄悄地對魏特琳說,不要讓年輕的女性回去,她們應該留在安全區里。
2月18日,迫于日軍的壓力,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更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安全區不復存在。
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雖然從未像設立者期望的那樣安全,但根據后來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安全區還是收容、救濟了20萬至30萬的中國難民,讓他們免遭屠戮。這樣的數字讓人不寒而栗——南京淪陷時,滯留城內的中國人約有50萬人,也就是說,安全區之外,南京幾乎被屠殺一空。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更名的前一天,拉貝回國。臨行前,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他舉行了告別茶會。消息傳出,數千中國難民聚集到學校的大草坪。拉貝走出來與大家告別,數千人忽然跪地大哭,請求他不要離開。
拉貝在日記中寫道:“這一切聽上去十分傷心和夸張。但誰要是也見過這里的悲慘情景,就會理解我們給予這些人的保護意味著什么。其實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并不是我們的某種英雄品質。”
在當天的告別詞中,拉貝說:“我一定不會忘記,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樣率領400名女難民穿過全城,將這些人送進我們安全的收容所里的,這只是無數事例中的一個。”
魏特琳依然選擇堅守。她在日記中寫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大門又一次敞開了。如果能為她們做點什么,我一定盡力。”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收容所一直堅持到1938年5月底,安全區內最后的6個難民營都徹底關閉。在那之后,魏特琳仍以暑期辦學的形式收留著約800名婦女。
安全區的新生命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部分難民合影。
下午在實驗學校校園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惡心。我的狗萊蒂叼來一顆小孩的頭顱,可能是被拋棄的或沒被掩埋好的尸體。
——1938年3月1日《魏特琳日記》
日本軍隊在南京大規模的屠殺告一段落之后,往日繁華的南京城已如人間地獄。
魏特琳和程瑞芳還以女性特有的對生命的敏感,記下女人在戰爭中的特有的際遇:懷孕、生產。血流成河沒有讓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新生兒誕生的啼哭,像是為抗議殘暴的殺戮而鳴。
在南京大屠殺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金一虹教授負責了“大屠殺期間的金陵難民所”課題。“魏特琳的日記里記載,有37名嬰兒降生,他們挨過了災難嗎?”金一虹嘗試著尋找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們的母親呢?他們的家人呢?”
遺憾的是,金一虹的尋找并沒有帶來太多的收獲。“我們能找到的,確切出生在南京淪陷后難民營里的人,還非常少。”
沈慶武是為數不多的被尋找到的安全區新生兒之一。
沈慶武出生于1938年1月17日。他從父母那里聽說自己初臨人世時的場景:在一幢教學樓的樓梯下面,40歲的母親生下了他。11歲的姐姐拿著剪刀剪斷了臍帶,當起了接生婆。
安全區里幾乎每天都有生有死,在惡劣條件下,有的孩子得了白喉、腹瀉、瘧疾,悲慘地死去。魏特琳想法為苦難的孩子搞到一些奶粉和魚肝油。因為很多中國貧苦婦女不會用奶粉喂嬰兒,程瑞芳和她的三個助手除了忙于接生、找藥,每天還要給幾十個嬰兒喂牛奶,給240名12歲以下的孩子喂魚肝油。
很多初臨人世的新生命,還沒有來得及看上這個世界一眼,就流星一樣逝去了。據魏特琳記錄,生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嬰兒有37個,死亡27個。
戰爭給女性帶來的還有另一重苦難,就是如何處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債。金一虹介紹,美籍醫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記中記敘,幾個月以來,許多不幸的婦女前來要求“卸掉”“不受歡迎的包袱”——她們都是因為被日軍強奸而懷孕。
史德蔚信奉基督教,反對墮胎,但他還是為那些婦女做了手術。他認為“遭強暴而懷孕的情況下墮胎為合法行為”。
魏特琳的日記也有過記載,她探望過29個可憐的棄嬰。他們被遺棄的原因是他們的父親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個小家伙大概活不長了,他們幾乎都有梅毒。
魏特琳此時也希望以宗教撫平悲慘女人們心靈和肉體的創傷。在沈慶武出生后的6周內,魏特琳安排每天兩次聚會,一次為成年人,一次為新生的孩子,由美國圣公會留守的5位牧師來布道。
女人們很快學會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這些女人特別喜歡唱的是《上帝,請拯救我的國家》、《我們熱愛養育我們的土地》。
沈慶武出生一個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來的住處安樂里。安樂里并非“安樂之地”。日軍的大肆殺戮停歇后,危險仍然時常光臨。“有一天,一個日本兵來到我家,讓父親對著墻壁站著,我父親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彎腰去撿時,日本兵的槍就響了,子彈擦著父親的頭皮飛過。”父親大難不死。
1938年5月底,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結束了作為安全區收容所的使命。但還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是無家可歸的婦女滯留在這里。魏特琳沒有顧忌日軍的命令,仍舊讓這些婦孺留在這里,甚至打開大門,又收留了原屬于其他難民營的女性。
張連紅說,這時候,安全區的概念已經不復存在了。魏特琳必須為收留這些婦女找一個理由。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一所大學,最恰當的理由就是開辦“培訓班”。
從1938年3月開始,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創辦了22個難民學員班。教育的內容從掃盲到小學、高中水平各異。隨后又設立職業訓練班,教給她們織手巾、襪子等謀生的手藝。9月,她又為170多個失學女青年辦了一所女子實驗中學。
這些培訓并不只是應付日軍的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也確實是為了婦女們未來的生計。這些教育被分為“職業科”和“家政科”。魏特琳在日記中對教育的成果很滿意,卻也語含諷刺地說自己“教育出了出色的難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潰。
——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給朋友的信
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寫下了她在中國的最后一篇日記。日記的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盡了。”此前的半年中,她在日記中多次留下過這樣的字句。日記也變得斷斷續續,有時甚至一個月也沒有寫下一字。
即便是在南京大屠殺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也沒有流露過一絲放棄或絕望的情緒。那些人性泯滅的屠戮、虐殺、強奸……漸漸成了記憶,時間卻沒有沖淡親歷者的創傷。魏特琳是見證者,眼見或耳聞的那些殘酷和苦難,卻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斷激蕩、發酵,漸漸壓垮了她的神經。她患上了嚴重的憂郁癥。
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回美國治病。
1941年5月14日,在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打開了廚房的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55歲。
魏特琳去世后,朋友們在她的枕邊發現了一張沾滿淚水的照片。那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避難孤兒的合影。
魏特琳被安葬在美國密歇根州雪柏鎮的一座公墓。美國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為她制作了一塊大理石墓碑,上面刻著中國古典式房屋的圖案。房屋頂部,用中文隸書寫著“金陵永生”四個字。在那座小鎮,沒有人理解這四個屬于東方古國的文字。
在南京期間,魏特琳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她的日記郵寄給美國的朋友。這些對南京大屠殺的記錄,曾陸續發表在美國俄亥俄州的一本雜志上,但并沒有受到關注。
20世紀8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整理海外傳教士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的原稿,并將其整理公開,供學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美麗的東方女子眼含淚水,在耶魯大學讀到了這部用打字機打印、長達526頁的日記。這位女子叫張純如,美籍華裔作家,正在為她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收集歷史資料。
1998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讓張純如一舉成名。這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軍隊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的歷史讀物。
張純如在她的書中對魏特琳這樣描述:“在一個幾乎變成虛構的傳奇中,由于天天面對日本人的殘暴的行為,一個脆弱的、疲憊的女人永遠無法恢復其身心所受的創傷,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這句話,卻也成了張純如對自己的心靈解說。
南京大屠殺沉重得讓人窒息。創傷刻在了一個民族的肌體上,讓每個有良知的人不忍直視。它像地獄的噩夢,震顫著人的心靈。
和魏特琳一樣,試圖探究這場噩夢的張純如也患上了抑郁癥。2004年11月9日,美國加州的一輛汽車里,張純如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選擇了同樣的方式毅然告別這個世界,年僅36歲。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
如遇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相關文章刊發之日起30日內與本網聯系。版權侵權聯系電話: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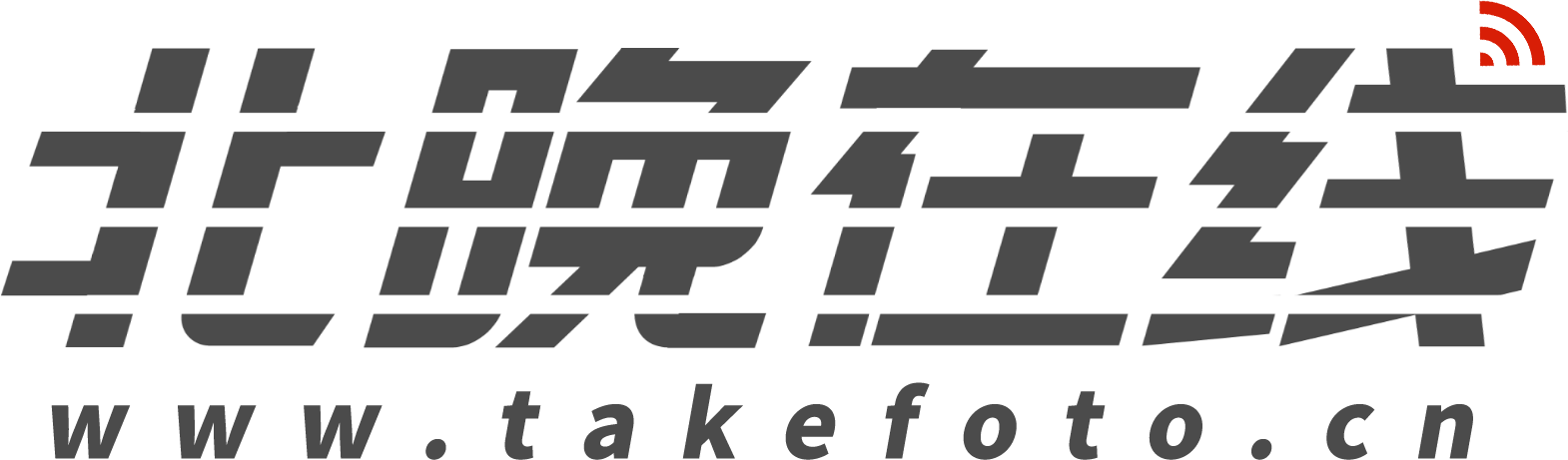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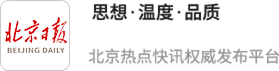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未登錄
全部評論
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