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由茅盾文學獎改編的電視劇《北上》熱播,讓原著作者徐則臣再度為大眾目光所聚焦。作為北京作協(xié)副主席、《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這些年的事務工作越發(fā)繁忙,但他依然保持著走上寫作道路之初時的勤勉,今年下半年又結集出版了《域外故事集》。書名化用魯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以一個在各國漫游的中國作家口吻,講述了十個發(fā)生在國境之外、亦真亦幻的故事。書鄉(xiāng)近期和徐則臣對話,與其說是采訪,更是一個作家懷著真誠內(nèi)省之心,對自己的寫作理念及技法展開的思索與漫想。

世界故事與中國傳統(tǒng)
書鄉(xiāng):您以前的短篇小說很多都是以故鄉(xiāng)或北京為中心展開的,而《域外故事集》將足跡拓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且這十個故事中,前兩篇《古斯特城堡》《去波恩》是2010年寫的,后面八篇都是集中在這兩三年寫的。為什么會有這么大、這么久的空間時間跨度?
徐則臣:我并沒有刻意要去轉(zhuǎn)變,因為我的生活軌跡就是這樣的,不同時期對不同地方的熟悉程度不一樣,一開始是對老家更熟悉,到了北京后,也是等到覺得對這座城市有了整體的認知、有能力和角度把感受表達出來時,才會動筆。2010年左右,我開始頻繁出國,自然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印象、見聞想表達出來。當時我的確是想寫一個域外系列,但寫完這兩篇之后,沒有接著寫,又去寫了些別的,包括《北上》。寫作就是這樣,一旦那股勁兒斷掉了,就很難再撿起來。但還是有點不甘心,想著將來要整體寫出來,所以即便有些相關素材可以在其他小說里涉及到,我都避開了,留著。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寫,直到疫情期間,哪里也去不了,無論從現(xiàn)實意義還是抽象意義上都想透口氣,就把曾經(jīng)這些一直想寫沒寫的東西一點點撿起來,寫了這個小說集。

書鄉(xiāng):這十多年里,外部世界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再回顧起來,比起十幾年前剛嘗試寫域外故事,有沒有一些新的感觸?
徐則臣:如果沒有疫情,沒有這種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我可能不會這樣寫,也許還會像《古斯特城堡》《去波恩》那樣,更多地去寫一個中國人在國外的見聞或者鄉(xiāng)愁,就是那種比較傳統(tǒng)的異域生活寫法。而且這些年間,我個人對短篇小說的認識也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如果再那樣寫,我會覺得有點不夠興奮,構不成挑戰(zhàn),激發(fā)不起更強烈的寫作和表達欲望。這兩年我一直在看《聊齋》、“三言二拍”,琢磨如何把這里面的一些敘事手法融進去,所以比起前兩篇還屬于現(xiàn)實主義的邏輯,后面幾篇就會不斷出現(xiàn)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懸疑感會更強一些,甚至有一些超現(xiàn)實的部分。
書鄉(xiāng):除了《聊齋》,還看到劉亮程老師評價說這本書讓他想到了從前閱讀《鏡花緣》的感覺,讓我很有同感,雖然講的故事不一樣,但是這樣一個四處游歷的中國人講海外奇妙故事的敘事基底是非常相似的。這是一種對傳統(tǒng)資源很有創(chuàng)造性的調(diào)用。經(jīng)過這些年的閱讀和試練,您是不是已經(jīng)基本找到了把傳統(tǒng)文學和世界文學接上頭的對接點?
徐則臣:提到《鏡花緣》,李汝珍就長期住在我們老家連云港(笑)。關于傳統(tǒng)文學,我做了一些自己覺得還挺有意思的嘗試。現(xiàn)在也有很多人在重寫傳統(tǒng),但基本上是寫舊的故事,寫花妖狐媚,但我希望能用它們來處理當下生活,能在不同民族、種族之間產(chǎn)生碰撞和融合。但怎么把《聊齋》《鏡花緣》式的邏輯從古代拿來處理當下,難度挺大的,沒有人提供一個非常成熟的范式。這個有點像徐悲鴻用中國畫的方式去畫馬,卻畫出油畫的感覺,也像郎靜山的攝影,用現(xiàn)代的攝影技術創(chuàng)造出古代山水畫的效果。我也希望能有這種感覺。說實話,我一開始沒有那么自信。這批小說里面,首先用這個技法寫的是關于吉卜賽人的《瓦爾帕萊索》,這也因為吉卜賽人本身就充滿了神秘感,我就以此往下延續(xù)。通過幾個小說操練,慢慢就有感覺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現(xiàn)實到底是什么樣子?過去我的小說里面呈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實,都可以經(jīng)得起現(xiàn)實主義邏輯的推敲,但其實很多事未必都合轍押韻,常常是溢出日常邏輯的,但那也是現(xiàn)實。所以我就想寫得既不那么匪夷所思,又有所溢出,同時還是藝術的,有美感,有意味。因此一直在不停調(diào)試和糾錯。
作家的魔法
書鄉(xiāng):我一開始讀的時候,感覺很像一個作家的海外游記,特別是里面的敘事人“我”就是個姓徐的作家,去全世界參加文學活動,還寫了《王城如海》《如果大雪封門》(徐則臣代表作)等作品,很容易與您本人等同起來。但是接著往下讀會發(fā)現(xiàn),每一篇都會在某個說不清楚的時刻,忽然跨過了現(xiàn)實和虛構的界限,于是頓悟“我”本質(zhì)是一個虛構人物,是一個用“披頭散發(fā)的英語”在全世界行走、觀察并深度參與的一個新型中國作家形象。您對于這樣一個作為文學形象的作家,有什么樣的構想呢?
徐則臣:剛開始寫前兩三篇的時候,我都沒太在意,第一人稱順手,就拿來寫了。到寫《瑪雅人面具》時,開始猶豫到底要不要讓讀者跟我本人聯(lián)系起來。我嘗試用第三人稱來寫,但試了一下就放棄了——為什么非得避開自己呢?是否能讓讀者看起來覺得像真實的游記,但讀著讀著又發(fā)現(xiàn)并非紀實?我想看看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干脆就一以貫之。寫《紫金洞》這篇時還曾想過讓“我”當一個醫(yī)生,后來也放棄了。我想既然是主題系列,總得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比如敘述視角和身份。我希望讀者在讀的時候,一會覺得跟我有關系,一會又覺得沒關系,注意力一會被“我”吸引,一會又覺得“我”也不重要。如果能實現(xiàn)這個效果,我作為作家,就會覺得自己的魔法奏效了。
書鄉(xiāng):我覺得最有魔法的一篇是發(fā)生在白俄羅斯的《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里面的敘述人“我”是不停變換的,有一位甚至是您之前小說《如果大雪封門》里的人物林慧聰,讓作家和自己的虛構人物對話,又讓這個虛構人物和小說中另一個虛構人物冰釣者對話,把純虛構擺在面上,但讀來似乎又很真實。
徐則臣:那個冰釣者形象的確是來自白俄羅斯,有一年我去明斯克參加活動,參觀一個烈士陵園,那里有一大片湖,當時零下20攝氏度,結了非常厚的冰,可以從湖上直接走到紀念碑前。就在白皚皚的冰面上,有一個男人坐在那兒冰釣,穿黑衣服,一動不動,像個雕塑。當時我覺得特別震撼,有種地老天荒的感覺,天寒地凍,是什么原因能讓他一直坐在那里?我就很想虛構他的生活。我又想到曾經(jīng)寫過的林慧聰,他是個南方人,卻渴望寒冷,當年就為了看一場封門的大雪來到北京。把他放在更冷的明斯克會怎樣?把這兩個人放在一塊兒會怎樣?出于這個想法,我讓兩個虛構的人處于一個非常具體的語境里,讓他們本身的生活運行軌跡碰撞,看能不能反而產(chǎn)生一種真實的感覺。

書鄉(xiāng):就像這個冰釣者,您也曾提到好幾篇的寫作靈感都源于在某個地方游歷的一些真實片段。如《瑪雅人面具》里買面具的情節(jié),《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里機場丟失行李箱的遭遇,都是發(fā)生在您本人身上的真事。而且準備寫這系列時,回憶中的域外素材是很多的,經(jīng)過一番過濾、篩選,最后才選定了這十篇。這里面其實就是一個將經(jīng)驗轉(zhuǎn)化為虛構文本世界的過程,對您來說,這個過程是如何發(fā)生的?
徐則臣:我去過差不多30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有時是一個場景,有時是一個人物,但都是碎片化的。當時在梳理時,就先把這么多年在我內(nèi)心顛來顛去、還沒有從篩子漏下去的那些有意思的細節(jié)捋出來。寫了這十個,還剩一些材料,也許若干年后,還會把那些滾成結石的東西寫出來。但它們暫時還是一堆散金碎銀,我不知道到底怎么用,得找到跟它相關的那些虛構的現(xiàn)實,能把它編織到某種關系中,又有足夠的意味,可以撐起一個短篇,那時我會再寫它。
故事或小說在我看來就是一堆元素的關系的總和,這些元素看起來不相干、不搭界,但只要能給它們建立經(jīng)得起推敲的聯(lián)系,且還特別有意思,這個小說就成了。
寫作的魅力
書鄉(xiāng):書的扉頁寫道“在地球每個角落與中國重逢”,里面寫到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中國人,有的有“母語鄉(xiāng)愁”,有的又竭力想和故鄉(xiāng)切斷聯(lián)系,還有的“疑似”中國人,他們可以說是 “我”在域外和中國重逢的最直接的通道。對于這樣一些域外中國人,您有獲得哪些新的靈感,或賦予了哪些新的特質(zhì)?
徐則臣:出國見到的中國人對我們來說都是老鄉(xiāng),同時他們又在異鄉(xiāng)文化里面沉浸了多年,有一定的體認,這種“腳踩兩只船”恰恰讓我覺得有意思。但他們有一些骨子里的東西還是不變,像《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里,在美國任教的馮教授特別喜歡做紅燒肉,我們和域外中國人之間,就靠語言、鄉(xiāng)愁、紅燒肉這些東西來連接。《瓦爾帕萊索》里陪“我”在智利訪問的宋老師在小說里好像也沒起到多大作用,但這樣一個人在中國人和拉美人之間,就像是一個潤滑劑,我們需要借助他來和其他文化對接。這系列小說很多人反映讀著挺絲滑,沒有疙疙瘩瘩,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寫的過程中,腦子里是有一個現(xiàn)場“翻譯”在的,他把兩種文化糅合到一塊,相互調(diào)和轉(zhuǎn)譯,讓彼此之間能夠迅速實現(xiàn)理解。
書鄉(xiāng):還有一個有意思的點,您本人是喜歡跑步的,小說集里的這個作家“我”也經(jīng)常跑步。跑步這件事有時跟文本有關系,像最后一篇《邊境》就是個關于跑步的故事,有時又沒有關系,只是一個日常活動,但也會專門寫一筆。所以好奇跑步是不是跟您的寫作,或者和文本的內(nèi)在節(jié)奏有某種相關性?
徐則臣:你要不說,我還真沒在意這個。這些小說的節(jié)奏感與語言的速度,確實比我其他小說要快。我在國外的確是經(jīng)常跑步,是我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在回想國外生活場景的時候,節(jié)奏一直都是很快的,也許是把跑步的感覺帶進來了,最后投射到了寫作中。我寫的“花街”系列,就是在運河邊上的故事,整個節(jié)奏是緩慢的,像水流。
《邊境》這個小說,當時是和李敬澤老師等人相約寫一個關于跑步的作品,李老師后來出了一個《跑步集》。我有一次去了一個邊境,兩個國家挨得很近,界河兩側(cè)各攔著鐵絲網(wǎng),下面各有一條很窄的小路,對面的情況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相互可以打招呼。經(jīng)過這個地方我就想到,如果在這里跑步會怎么樣?要處理哪些問題?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故事。
書鄉(xiāng):我讀的感受就是您特別擅長把日常活動經(jīng)驗絲滑地融入到文學經(jīng)驗中去。
徐則臣:我覺得這就是寫作這件事有魅力的地方。比如說現(xiàn)在我一個人在外面走,凍得要死,但是可以抽煙,很舒服,那我回頭寫的時候,可能就把這個感覺寫進去了(笑)。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如遇作品內(nèi)容、版權等問題,請在相關文章刊發(fā)之日起30日內(nèi)與本網(wǎng)聯(lián)系。版權侵權聯(lián)系電話: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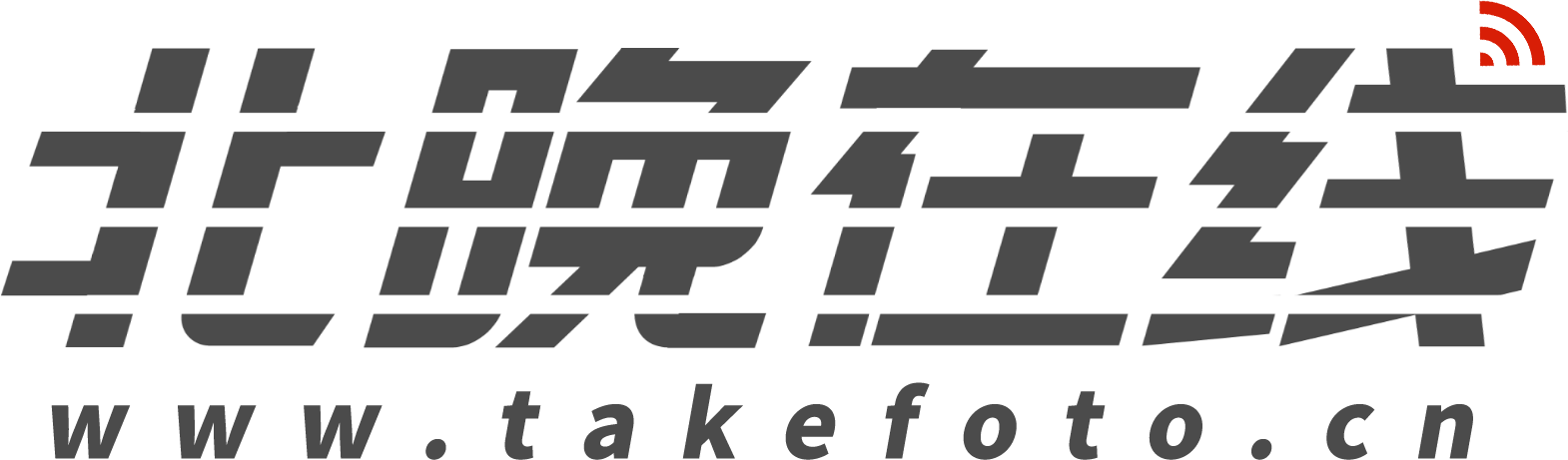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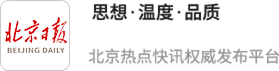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未登錄
全部評論
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