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書法“尚意”思潮的本質,并非對唐代“尚法”傳統的簡單否定,而是通過對藝術內核的重新審視實現創造性轉化。黃庭堅作為“宋四家”中理論建構最系統的書家,其書論散見于題跋、書信與詩文,卻始終貫穿著一種獨特的“轉化”思維——既非機械繼承晉唐傳統,亦非盲目顛覆法度規范,而是以人格修養為根基、禪學智慧為工具、詩書素養為滋養,對書法的審美范疇、創作方法與藝術邊界進行系統性重構。本文以“轉化”為核心線索,剖析黃庭堅如何將晉人之“韻”轉化為“韻勝”的人格化標準,將禪宗之“悟”轉化為“觀悟”的創作方法論,將詩書之“意”轉化為“書畫同法”的跨界思維,進而揭示其書論對中國書法“技道合一”傳統的升級意義,為當代書法處理“傳統與創新”的核心命題提供歷史鏡鑒。
從晉“韻”到“韻勝”
晉代書法“尚韻”的審美追求,雖已蘊含“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趣,但多以筆墨形式的含蓄蘊藉與風度氣韻為主要載體,如宗白華所言“晉人風神瀟灑,不滯于物”,其“韻”更多是一種自然流露的生命狀態,未形成明確的人格化理論界定與價值指向。黃庭堅的核心突破,在于將這種模糊的審美范疇轉化為以“人格修養”為內核的“韻勝”標準,使“韻”從單純的形式審美升格為“書品即人品”的價值判斷體系。
黃庭堅對“韻”的轉化,首先體現為“去俗”與“道義”的深度綁定。他在《跋周子發帖》(見《山谷題跋》卷四,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28頁)中直言“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將“不隨世碌碌”的人格獨立性作為“韻”的前提;更在《書嵇叔夜詩與侄榎》(見《黃庭堅全集·別集》卷十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5頁)中強調“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明確將“道義”與“圣哲之學”作為“韻”的精神內核。這種轉化徹底改變了“韻”的內涵——晉人之“韻”常因天賦與風度自然流露,而黃氏之“韻勝”則必須通過后天的人格錘煉與學養積淀獲得。他批評王著“美而病韻”、周越“勁而病韻”,根源并非二人技法不足,而是“靈府無程”的學養缺失,即“雖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周子發帖》)。這種評價標準的轉化,使書法審美從“形式判斷”轉向“人格判斷”,構建了“人書合一”的審美新范式。

《花氣薰人帖》
紙本 30.7cm×43.2cm
約元符三年(1100)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此帖為山谷少見的小品之作,不像其大草狷狂恣肆,而是多了小草的悠閑自得,一片爛漫天真之態。此作第二行,筆法尚在行草之間徘徊,正是花香擾禪“欲破不破”之際。從第三行開始,干脆“破而后立”,一瀉千里,任其流轉,用筆圓勁剛健,軸線自然擺動,墨色濃潤枯澀皆有,如同作者本身將歲月、春天、創作等復雜的人生經驗融于一體,韻味十足。
其次,黃庭堅將“韻”的表現維度從“單一形式”轉化為“多維統一”。在技法層面,他提出“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要求線條質感在剛柔相濟中體現生命力,如褚遂良書“豪勁清潤”、李后主筆“力不減柳誠懸”,均因達到“骨肉平衡”而具“韻”味;在章法層面,他推崇“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馀”(《論書》),認為空間處理的疏密得當是“韻”的視覺載體;在精神層面,“韻”則表現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超越性,與禪宗“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境界相通。這種多維轉化,使“韻”從抽象的審美感受變為可實踐、可鑒賞的具體標準,解決了晉代“尚韻”理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局限,為宋代“尚意”書風提供了清晰的審美導向。

《致云夫七弟尺牘》(局部)
紙本行書 32.6cm×65.4cm
年份不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云夫七弟得書。知侍奉廿五叔母縣君萬福。開慰無量。諸兄弟中。有肯為眾竭力治田園者乎?鰥居亦何能久堪。復議昏對否?寄示兄弟名字曲折。合族圖。幾為完書矣。但欲為其中有才行者立小傳。尚未就耳。龐老《傷寒論》無日不在幾案間。亦時時擇默識者。傳本與之。此奇書也。頗校正其差誤矣。但未下筆作序。序成先送成都。開大字板也。后……
此帖是山谷傳世書札中文字最長者,也是其簡札尺牘中較為穩定的一種風格。不同于其瀟灑爛漫的小行書,此篇用筆純正規范,不激不厲,風規自若。結字由扁平趨于方正,再趨修長。章法則于平淡之中見顧盼之姿,行布極富神韻。整篇氣息含蓄內斂,也符合他自己對于“韻”的追求。
從“臨摹”到“觀悟”
唐代書法“尚法”傳統下,學習路徑多以“臨摹”為核心,強調對法度的精準復制,如歐陽詢《八訣》、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均以技法規范為論述重點。黃庭堅則將禪宗“頓悟”思維與“不立文字”的修行方式轉化為書法創作方法論,構建了以“觀悟”為核心的學習體系,實現了從“機械摹形”到“精神會意”的方法論革新——需說明的是,他并非否定“臨帖”的基礎價值(其早年亦有“臨摹凡十年”的實踐),而是以“觀悟”補充“機械臨摹”的局限。
黃庭堅對創作方法的轉化,首先體現為“讀帖(觀悟)”對“機械臨帖”的補充與升華。他在《跋與張載煦書卷后》(見《山谷題跋》卷五,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56頁)中明確提出“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這里的“觀”并非簡單的視覺觀看,而是融入禪意的“觀照”——如禪宗“觀心”般體悟古法背后的精神內核,而非執著于筆畫的外在形態。他自述“紹圣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書草老杜詩后》),正是通過“觀”山水自然與禪宗公案,悟得“疾舒險夷之道和習熟自然之理”;晚年觀艄公“長年蕩槳,群丁撥棹”(《跋山谷草字》),更將自然動態轉化為草書的筆勢節奏,實現“筆墨隨天機流轉”的創作狀態。這種“觀悟”方法,打破了唐代“字字臨摹”的機械性,使古法學習從“技術復制”轉化為“精神對話”,正如他所言“會之于心,自得古人筆法也”(《論書》),構建了“以心傳心”的傳承路徑。


《廉頗藺相如傳》(局部)
草書 卷軸 紙本
32.5cm×1822cm
年份不詳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釋文: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原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
此作品深得懷素草書遺意,尤其能展示其懸腕攝鋒運筆的高超技藝。其用筆圓通,線條凝練多變,字勢奇逸,連綿不絕,如龍搏虎躍而又圓婉超然。結體移形變位,行間俯仰欹側,左右開張,穿插錯落。墨色枯潤相映,布白天趣盎然。可謂氣勢豪邁,超凡脫俗,似有禪家氣息,又有極強的韻律感,令觀者的心境也隨著線條在紙面上跌宕起伏。
其次,黃庭堅將禪宗“句中有眼”的思維轉化為“字中有筆”的技法要求。他提出“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論書》),禪宗“句眼”是破除迷障、直指本心的關鍵,而書法“筆眼”則是蘊含精神力量的筆法核心——即通過一筆一線傳遞書家的人格意趣,而非單純的技法痕跡。他反思早年書法“用筆不知禽縱,故字中無筆”(《自評》),正是因為執著于筆法的外在形式,未能領悟“筆”背后的生命意識;而晚年書法“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跋自書》),卻因突破形式束縛,使“筆”成為精神的直接流露,達到“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的境界。這種轉化,使技法學習從“筆法規范”轉向“精神灌注”,如他評楊凝式書“如散僧入圣”(《跋楊凝式帖》),正是因為楊凝式突破“小僧縛律”的法度桎梏,以“筆眼”傳遞“蕭散簡遠”的人格精神,實現了“無法而法”的創作自由。


《砥柱銘卷》(局部)
卷軸 紙本 墨書 32cm×824cm 私人收藏
釋文:維十有一年,皇帝御天下之十二載也。道被域中,威加海外;六和同帆(軌),八荒有截;功成名定,時和歲阜。越二月,東巡狩至于洛邑,肆覲禮畢,玉鑾旋軫;度崤函之險,踐分陜之地;緬維列圣,降望大河;砥柱……
詩書禪互滲
中國傳統藝術歷來存在“詩書畫印”的交融趨勢,但在北宋之前,各藝術門類仍保持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詩歌重“言志”,書法重“傳情”,繪畫重“狀物”,尚未形成以“技法同源”為核心的跨界理論。黃庭堅的創新之處,在于將詩歌的“意趣”、禪宗的“頓悟”與書法的“筆法”相互轉化,構建了“詩書禪互滲”的藝術觀,并提出“書畫同法”的跨界理論,實現了藝術邊界的創造性突破。
黃庭堅對藝術邊界的轉化,首先體現為“論書詩”的詩書互滲。作為江西詩派創始人,他將書法的審美理念融入詩歌創作,形成獨具特色的“論書詩”。如“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既為“學書需創新”的論書主張,亦為“作詩忌模仿”的詩歌準則;“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嵇叔夜詩與侄榎》),既強調書法需以人格修養為根基,亦彰顯詩歌“言有物、行有格”的傳統。這種互滲并非簡單的“以詩論書”,而是將詩歌的“韻外之致”與書法的“筆外之意”相互轉化,使“韻”成為詩書共通的審美核心——詩歌的“韻”體現為“語少而意密”(《評魏晉人書》),即通過凝練語言傳遞深層意趣;書法的“韻”體現為“筆簡而神足”(《跋褚遂良帖》),即通過簡約筆墨傳遞人格精神,二者均指向“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正如他評魏晉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跋王右軍帖》),實則是將魏晉詩文的“韻”與魏晉書法的“韻”視為同源,實現了詩書審美的本質統一。

《牛口莊題名卷》(局部)
絹本行書 25cm×1004cm 元符三年(1100)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釋文:……壺奕棋,燒燭夜歸。此字可令張法亨刻之。
此卷為黃庭堅傳世墨跡中最大的行書作品,記錄了他與廖致平投壺對弈的雅興。他以羊毫飽蘸墨汁,筆筆圓渾飽滿,藏露自如,行筆迅捷,以腰帶肩,以肩帶臂,以臂帶腕,以腕運紙,筆力扛鼎,大氣磅礴。同時,其在醉酒中依然筆勢連貫且不逾規矩,達到“器物相合”“心手合一”的“無我之境”。
其次,黃庭堅提出“書畫同法”的理論,將書法的筆法轉化為繪畫的筆墨語言,且明確二者“技法同源”的核心在于人格修養的灌注。與蘇軾“詩畫一律”(《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強調“意境相通”不同,黃庭堅更注重“筆法共通”——“用書法寫畫,是用筆的不俗”(《跋李漢舉墨竹》),明確指出書法與繪畫在筆法上的共通性:書法的“長槍大戟”式線條需“骨力內含”,繪畫的“披麻皴”式筆墨需“氣韻連貫”,而二者的“不俗”均源于書家(畫家)“胸中有道義”的人格修養。如他評文同畫竹“胸有成竹,下筆如飛”(《跋文與可墨竹》),實則是文同將書法“意在筆先”的筆法理念轉化為繪畫創作,使竹畫的“墨色濃淡”如書法的“線條枯潤”般傳遞精神意趣;而他自身亦以書法筆意作枯木,被蘇軾評為“胸中有千駟,不落筆墨蹊徑”(《東坡題跋·跋山谷墨竹》)。這種轉化,打破了“書法為線條藝術,繪畫為形象藝術”的傳統界限,使筆法成為連接書畫的核心紐帶——書法的筆法賦予繪畫以“骨力”,繪畫的意境賦予書法以“氣象”,二者在“韻勝”的審美標準下實現統一,最終達成“書畫同境”的藝術高度。

《致天民知命大主簿書》(局部)
紙本行書 25.5cm×45.9cm
紹圣二年(1095)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天民、知命、大主簿:霜寒。想八嫂、安裕、九妳、四妳、大新婦、普姐、師哥、四娘、五娘、六郎、四十、明兒、九娘、十娘、張九、咩兒、韓十、小韓、曾兒、湖兒、井兒,各安樂。過江來,甚思汝等,寂寞且耐煩。不須憂路上,路上甚安穩。但所經州郡多故舊,須為酒食留連爾。家中上下,凡事切且和順。三人輪管家……
此帖亦稱《與天民知命書》、《天民知命帖》,是黃庭堅寫給其弟天民、知命及侄子大主簿的一封家書。黃庭堅在信中寫下對親人的關懷與問候,這時他的書法技藝已經爐火純青。從筆法上看,中鋒行筆,運筆自如,使轉流暢,線條圓厚且富有變化。從結構上看,其小行書謹嚴周密,既有楷書的規整,又有行書的靈動。從章法上看,此作不同于他平穩工整的小行楷,多用字組連帶,行距疏密有間,行筆抑揚頓挫,節奏分明。
結語
從宋代至今,黃庭堅的“轉化”思維始終影響著書法藝術的發展——明代徐渭從“黃庭堅草書”中悟得“狂放精神”,形成“筆走龍蛇”的狂草風格;清代何紹基以“黃庭堅書論”為指導,融合篆隸筆法探索“中鋒用筆”的新表達。在當代語境下,這一思維更具現實意義:它為當代書法如何“傳承傳統而不保守,創新形式而不迷失”提供了歷史鏡鑒,也為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價值的思想資源——唯有把握“轉化”的本質,才能使傳統藝術在當代煥發生機,實現“古為今用”的文化價值。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如遇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相關文章刊發之日起30日內與本網聯系。版權侵權聯系電話: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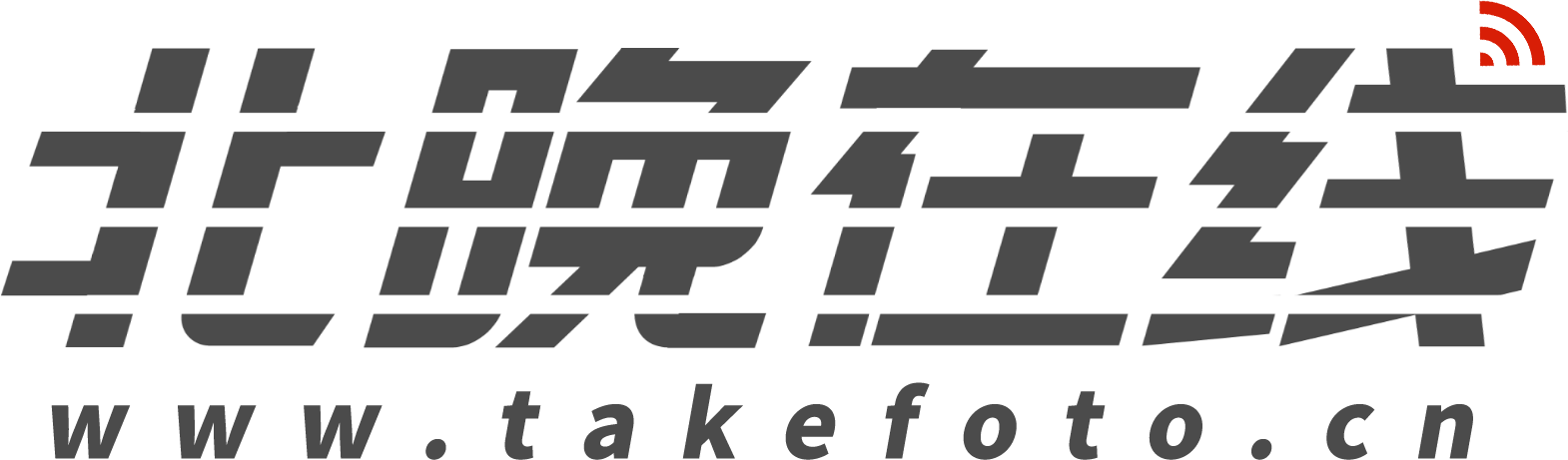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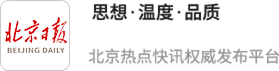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未登錄
全部評論
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