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日,在北京周口店龍骨山上,年輕的中國學者裴文中挖掘出了第一塊完整的古人類頭蓋骨化石。考古學界將這種古人類正式定名“中國猿人北京種”,簡稱“北京人”。
1936年,在中國考古學家賈蘭坡的主持下,在周口店又發掘出另外三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和一塊完整的人類下頜骨。周口店的發現,震動了全世界。
今天,北京日報紀事帶您一文回顧,“北京人”頭蓋骨從發現到消失的傳奇經歷。

“北京人”,被古生物學界稱為“古人類全部歷史中最有意義最動人的發現”。它的發現,為揭開人類起源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將人類自身歷史整整提前了50萬年;它的丟失,又給人類留下了一道世紀謎題。九十多年過去,各種傳說、猜測多方流傳,“北京人”在哪里的謎底卻始終沒有揭開。
雞骨山龍骨
眾所周知,“北京人”被發現于周口店龍骨山。這座山名來自這里的一種特產——龍骨。
在中藥典籍中,龍骨是一味藥材,其來源多被附上神秘色彩,說成“死龍之骨”、“龍蛻”。其實,龍骨是古代哺乳動物如象類、犀牛類、三趾馬等的骨骼的化石。在上個世紀初葉的中國,只有西方來華的科學家、考古學家能了解這個常識。這些人成了龍骨的“收集愛好者”。

1918年2月的一天,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北京得到了一小包帶著紅色黏土的骨骼碎片化石。送給他這份禮物的是一位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化學家,他饒有興味地告訴安特生,這些化石是他親自采掘的,出自周口店雞骨山的山崖,那座山就因為紅土中藏著大量鳥類骨骼而得名……
雞骨山所在的位置,一下子挑起了安特生的興趣。那源于一場懸而未決的爭論。
上世紀初,一位叫哈貝爾的德國醫生在北京買到了不少龍骨和龍齒。這位醫生雖不是研究古生物的專家,但很了解這些化石的學術意義。他把這批化石全部送給了著名的德國古脊椎動物學家施洛塞爾教授。
施洛塞爾在這些化石中,鑒定出了符合人類特征的兩顆牙齒,這是整個亞洲大陸破天荒的發現。
當時,人類起源的古生物學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第一次提出了人類進化是從猿到人的學說。與達爾文同時代的德國生物學家海卡爾支持達爾文的觀點,并斷言猿與人之間存在著譜系上的聯系,同時,從猿到人之間存在一個尚待證實的中間環節:“缺環”。他說,“缺環”混合了人和猿的特性,可稱為“猿人”。
1856年德國發現的“尼安德特人”,1891年爪哇島發現的“爪哇人”,已經顯示出人類進化史的只鱗片爪,但是受當時的科學認知水平所限,這些發現在科學界爭論很大,更不要說堅決否定進化論的宗教界了。
施洛塞爾最終沒有認定那兩顆牙齒屬于人類,沒能用這兩顆牙齒補上“缺環”,而是將其作為“類人猿”的牙齒公開發表。不過,施洛塞爾也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推論:未來的調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國找到新的類人猿、第三紀人類或更新世早期人類化石的材料。
施洛塞爾和哈貝爾都不知道那兩顆牙齒具體的出土地點,公布研究成果時只說是出自中國的直隸地區。安特生得到那包雞骨山化石時,馬上把兩處地點聯系在一起——雞骨山在周口店,當時正是直隸地界。
安特生是名噪一時的地質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探險家。他在中國的身份則是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北洋政府之所以看中安特生,不單因為是他在地質學領域的建樹,還因為他的國籍。當時,瑞典被認為是“少數幾個對中國沒有野心的西方國家”之一。
北洋政府為安特生開出了18000大洋的天價年薪。相同時期,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先生,薪俸最高時月薪為300大洋。而安特生的月薪相當于1500大洋。
安特生倒是不白拿這份高薪,來中國不久就找到了一處大型鐵礦,又先后主持或參與了調查北方煤田和其他礦藏的分布。與此同時,優渥的收入讓他有條件在“礦政顧問”本職之外,充分開展自己感興趣的田野考古調查。
在得知周口店雞骨山是“龍骨”產地之后,安特生馬上前往那里進行了實地考察。這大概是周口店地區第一次有目的的考古挖掘。遺憾的是,安特生只挖到了一些鳥類和嚙齒類動物的化石。
此后不久,河南發現了大批三趾馬化石和仰韶文化遺址,把安特生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不過,他沒有忘記周口店。1921年,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來給安特生當助手,就被派到了周口店雞骨山進行考古挖掘。
這年8月,安特生又特意帶著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生物學家葛蘭格前往雞骨山,一同指導挖掘。
葛蘭格可以說是當時古生物發掘技術的權威,但是無論是他還是年輕的師丹斯基,在雞骨山都沒有得到預期的收獲。原因很簡單,他們找錯了地方。
不過,正是在這個錯誤的地方,安特生遇到了自己的“幸運星”。在他所著回憶錄《黃土的兒女》中,安特生講述了這次極為幸運的轉折:
“正當我們在雞骨山發掘的時候,一位中年中國男子走過來說:‘在這里待下去沒有什么用,離這里不遠處有一個去處,你們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龍骨。’”
新的考古挖掘地點很快到達。這里距離雞骨山約2公里,是一處地勢較高的早已被廢棄的石灰礦。礦墻約10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狀陡立著,因為常年挖掘石灰石,礦墻很不穩定,似乎隨時都會倒塌。中年人指著一條礦墻的裂隙說:“龍骨就在那里頭,你們挖下去,保證有大的收獲。”
收獲果然很快出現,先是豬和鹿的骨化石,不久后又發現了一些白色帶刃的石片,像是人類原始起源時使用的簡陋工具。
安特生滿懷期許地對師丹斯基說:“等著瞧吧,總有一天這個地點將成為考察人類歷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如果有可能,你把這個洞穴一直挖空為止。”
但是師丹斯基并沒有堅持到把洞穴挖空。經過幾個星期的挖掘后,洞穴已經高懸在峭壁之上,危險性越來越大,只能暫時中止。1923年夏,在安特生的一再要求下,師丹斯基進行了第二次挖掘,同樣因為危險性而停止。
安特生不甘心就此罷手,師丹斯基卻無論如何也不答應再冒險了。他把能采集的化石都收集到一起,帶回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對周口店的調查發掘,沒有使安特生立即實現找到人類遠古遺骸的夢想。在1923年的《中國地質調查簡報》中,安特生甚至對周口店的考古挖掘只字未提。
其實,他的好夢已經成真,只不過當時未曾領會。
“北京人”
作為仰韶文化遺址的發現者,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學界名聲大噪。而周口店的考古一時沒有什么成果,被暫時擱置。直到1926年,瑞典皇太子的訪華之行,意外地給了安特生一個震驚世界的機會。
作為在華聲望最高的瑞典科學家,安特生在這年7月就接到了瑞典政府的信件,指派他安排瑞典皇太子的在華活動。安特生也想借此機會展示一下自己的考古成果。他在中國發現發掘的古生物化石,已全部運往瑞典供烏普薩拉大學研究所的維曼教授研究。安特生馬上給維曼教授寫信詢問那些化石的研究成果。
接到維曼回信的時候,安特生剛剛從日本迎接皇太子來到北京。打開厚厚的包裹,安特生欣喜若狂。維曼寄給他的是一份周口店發現的兩顆人類牙齒的研究報告,同時還有這兩顆牙齒的大量照片、幻燈片。
10月22日,北京協和醫院禮堂,中國科學界人士為瑞典皇太子舉行了歡迎大會和學術報告會。京津兩地的中外學者和知名人士齊聚一堂,會上致辭和做報告的中方代表,一位是中國地質調查研究所所長翁文灝,另一位是著名學者梁啟超。安特生最后一個出場,做了一篇震動世界的科研報告。
這份報告的名字叫《亞洲的第三紀人類——周口店的發現》。
安特生在報告中介紹了烏普薩拉大學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周口店)所發現的牙齒中一顆是右上臼齒,大概是第三臼齒。從照片看來,它那未被磨損的牙冠所顯示的特征本質是屬于人類的……另一顆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齒。”
“現在比較清楚,在第三紀末或第四紀初,亞洲東部確實存在人類或與人類關系十分密切的類人猿。這一點在史前人類學領域是至關重要的……周口店的發現,給人類起源于中亞的假說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在一連串鏈條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環。”
安特生最后給出了他的結論:“除了把它們(周口店所發現牙齒的主人)稱作‘人’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報告演講完畢,臺下靜默良久。即便在座的都是中外科學精英,也需要一定時間來適應這個結論的巨大沖擊。安特生似乎預料到這個反應,開始為眾人放映那兩顆牙齒的幻燈片,進一步講解。
臺下似乎剛剛反應過來,有人打斷安特生的發言,大聲提問。時任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北京大學地質系古生物學教授的美國科學家葛利普,仿佛還沒有從震驚中醒過神來,問了一個安特生剛剛在報告中闡釋清楚的基本問題:“‘北京人’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人類還是食肉動物?”
安特生立即回答:“來自周口店的最新消息是,我們的老朋友既不是一位男士,也不是一種食肉動物,而是走在猿和人兩者半路上某個階段的代表,而且還是一位女士呢!”
安特生說的這段話,既有對葛利普的認真回答,也摻雜著玩笑。“走在猿和人兩者半路上某個階段的代表”,說的其實就是“猿人”。而說“北京人”是位女士,純粹是針對葛利普稱“北京人”(Pekingman)時用了“man”這個男性詞,所以安特生幽默地改用了女性的“lady”。
不過,葛利普和安特生的這一問一答,倒是真的給“北京人”起了名字。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黃慰文告訴記者,“北京人”(Pekingman)這個名字當時是葛利普隨口一說,但是簡單明了,成了最通用的叫法。后來考古學家把周口店發現的人種命名為“中國猿人北京種”,簡稱“中國猿人”或“北京猿人”,但是最廣為人知的名字還是“北京人”。
“北京人”的發現,補上了人類進化史上的“缺環”。安特生作為“北京人”的發現者,永載科學史冊。不過,僅憑兩顆牙齒,這個“缺環”填補得還不能算完整。“北京人”震驚世界的同時,也遭受了與“尼安德特人”、“爪哇人”類似的質疑和爭論。在世界考古學界,即便是持進化論觀點的人,也是各言其說,莫衷一是。
最終打消爭論,讓“北京人”成為確證無疑的人類祖先,還需要北京人頭蓋骨以及石器、用火遺跡等一系列考古成果。
發現頭蓋骨
周口店發現“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一經傳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彈震撼了當時的科學界。致力于遠東特別是中國考察的科學家都向周口店集結而來。稍有一點科學考察知識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發現,只不過揭開了遠古人類帷幕的一角,更加輝煌的成果還在周口店等待著后來人發掘。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學大軍中,沖在前面的是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加拿大籍人類學家步達生。
步達生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關系,在發掘仰韶文化遺址時,安特生就邀請他參與工作,隨后又一起籌備以新疆為目的的中亞考察項目。安特生忽然公布的“北京人”發現成果,一下子吸引了步達生全部的科學熱情。憑借與中美兩國政府和美國大財團的良好關系,步達生很快給周口店的科學發掘拉來了“贊助”,并且把安特生個人色彩濃厚的考古發掘,升格為國際合作。
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為美國基督教會創辦,主要出資人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步達生的游說下,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部同意每年出資一萬兩千美元用于周口店考古發掘,由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聯合實施發掘計劃。
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于1913年,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地質科學研究機構,創建人是英國學成歸來的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家丁文江。其繼任者翁文灝,則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在中國地質學領域有著大量開創性的貢獻。正是他與洛克菲勒基金會達成了周口店科學考古合作協議,在協議中明確了至關重要的“北京人”化石權屬:“人類及類人猿化石”由步達生掌握,但“應永久保管在中國”。
“北京人”遺址的挖掘從1927年4月16日開始,當年發掘中最大的發現,是獲得了一顆完整的人牙,在當年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中,步達生宣布周口店的發現是人類進化史上的新屬新種,即“中國猿人北京種”。可是這個“學名”沒有流行開來,還是當年葛利普隨口說出的俗名“北京人”,被科學界和大眾廣泛接受并延續下來。
周口店發掘計劃進行到第二年,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對參與人員進行了調整,年輕的楊鐘健和裴文中兩人來到了周口店。
這一年,楊鐘健31歲,剛剛在德國獲得古生物學博士學位,由他主持周口店遺址的發掘。裴文中年僅24歲,一年前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當時負責管理工人賬目和協助楊鐘健工作。
中央地質調查所是中國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等諸多學科的發端處,除了前兩任所長丁文江和翁文灝,其成員大多是楊鐘健、裴文中這樣的年輕人,很多人后來都成為各自學科的領軍人物。而當時年紀輕輕的他們,就已經站在中國“年輕學科”的最前沿,歷史給了他們難能可貴的機遇。
在周口店,第一個得到機遇眷顧的是裴文中。
1929年,楊鐘健調往山西、陜西負責新生代考古項目,周口店發掘的主持人之職,落到了裴文中肩上。
隨著周口店遺址發掘深度不斷延伸,堆積物的體積也漸漸變得狹小起來。當深度已進入地下40余米時,狹窄的空間幾乎只能容下一兩個人的身影。正當裴文中考慮就此收兵時,卻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鑿穿了一個洞穴。
這個洞穴現在仍保存在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里,被稱為“猿人洞”。正是在這里,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發現了。
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

裴文中在后來的挖掘報告和回憶文章中,多次回憶過那個他一生為之激動的歷史時刻。上世紀80年代黃慰文和賈蘭坡共同撰寫《周口店發掘記》,曾找到過當時仍在世的挖掘工人,從不同視角補充了大量的歷史細節。
黃慰文告訴記者,當時從“猿人洞”洞口開始的發掘已經延伸了10米,洞內非常狹窄黑暗,只有裴文中和另外三個技工能夠進入。通常情況下,洞穴挖掘要點汽燈,但是因為這個小洞穴太窄,他們只好一手舉著蠟燭,一只手用錘鎬、鏟子小心翼翼地挖掘。
一個叫王存義的技工回憶,挖掘的動作很輕,傳到洞外只是窸窸窣窣的聲音。忽然,他在洞口聽到了裴文中激動地大叫一聲:“這是什么?是人頭!”
裴文中在回憶錄中描述,當時他是聽到一個人說,下面有一個圓圓的東西露出來,于是趕緊下去和技工一起挖掘,露出的部分漸漸清晰可辨,他這才情不自禁地叫起來。“人頭”二字剛出口,大家全都圍了過來。
幾根蠟燭的光亮聚在一起,清晰地照亮了圓圓的頭蓋骨頂部。
這個頭骨化石,一半埋在松軟的土層,一半在硬土之中。裴文中與幾個技工把周圍的雜土清理干凈,嘗試著取出頭蓋骨,它卻紋絲不動。
天色已晚,有人提議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壞。裴文中卻等不及了。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其實他已經在山中過了不知幾千百萬日夜,并不在乎多過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腦筋中不知輾轉了多少次,結果決定取出來,用撬杠撬出。”
裴文中找來撬棍,輕輕插于頭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動。不承想,這顆歷經數十萬年已成化石的頭骨,并沒有像石頭一樣堅硬,而是很脆。頭蓋骨撬下來的同時,有一部分也破裂了。
這讓裴文中極為懊惱,破裂可能造成的損傷還需要再勘察,眼前最棘手的,是怎么把這個破裂的頭骨不差分毫地帶出去。他急中生智,脫下自己的棉襖,把頭蓋骨輕輕包裹起來,這才抱著它躬身出了“猿人洞”。
據王存義回憶,頭骨剛挖出來時很潮濕,撬棍造成的破裂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點。整個頭蓋骨既酥軟又潮濕,稍一震動就發生爆裂。這種狀況,顯然無法安全無損地帶回北京。
裴文中帶著他和另外一個工人生了個火盆,待柴火燒成炭,采用沒有火苗和煙的炭火慢慢烘烤頭骨。頭蓋骨在逐漸的干燥中開始硬化,裴文中又在頭骨四周糊上五層棉紙,棉紙外再加石膏和麻袋片,經水浸泡后再度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上的一切和頭蓋骨形成一個整體。

整整烤了三天,裴文中才用他的兩床棉被把頭骨包裹起來,打成包袱背回北京。
在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步達生用別針一點點將包裹著頭骨的硬土剔掉,一顆頭骨完整地呈現在這位解剖學教授和古人類研究專家的眼前。
“沒錯,是人的!是人的!”步達生拍著裴文中的肩膀連聲高叫。
12月28日下午,中國地質學會特別會議在地質調查所隆重舉行,應邀到會的除科學界的大師名流外,還有中外新聞界人士。裴文中在會上作了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報告。
中國北京的周口店發現了最早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北京人”再次震驚了世界。有了這顆頭蓋骨的出現,即便是那些對牙齒化石持懷疑態度的人,也終于承認,“北京人”被發現了。
何去何從
1935年,三十歲出頭卻已經名滿天下的裴文中遠赴巴黎留學,歷史把機會賦予了一個當時只有高中文化的年輕人——賈蘭坡。

賈蘭坡1929年畢業于北京匯文中學,隨后考入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當起了練習生。練習生在研究部門職位最低,平時不但是考古專家的助手,還要和雇傭的工人一樣挖石背土。但練習生工作亦是學習,能和專家一樣接觸到最前沿的考古知識和成果。
1931年春,初到周口店不久的賈蘭坡就進入了重大成果發現的核心圈。當時他協助裴文中清理洞中的松軟堆積,收集到不少于兩千塊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數顯示出加工和使用過的痕跡。由此,裴文中大膽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遠古人類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結論。
與此同時,裴文中和步達生等學者根據周口店堆積層中燒焦的木頭和碎骨的痕跡,得出了北京人已開始用火的結論。
加工、使用工具和用火這兩項技能,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征。“北京人”被定義為人類,終于成了無可辯駁的事實。
這兩項考古成果,賈蘭坡都有參與,但是當時還沒有人注意到這個二十多歲的練習生。
1936年11月15日上午,周口店考古現場,技工張海泉把挖到的一塊核桃大的碎骨片,隨手扔進了身旁的荊條筐。在旁邊的賈蘭坡問是什么東西,張海泉答“韭菜”(碎骨之意)。賈蘭坡卻僅憑一瞥,就認定那塊碎骨的不同尋常。他拿起來一看,不禁大嚷:“這不是人的頭蓋骨嗎?”
賈蘭坡馬上命人用繩子把現場圍了起來,自己趴在地上親手挖掘。慢慢地,耳骨、眉骨也從土中露出來了。直到中午,這個頭蓋骨的所有碎片才被全部挖出。賈蘭坡將頭蓋骨送回辦公室,清理、烘干、修復,把碎片一點一點對粘起來。
當天下午,幾乎就在相同的地點,賈蘭坡又發現了一顆頭蓋骨。

當時世界著名古人類學家魏敦瑞正在北京,1934年步達生逝世后,他的工作就由魏敦瑞接替。得知周口店再次發現頭骨的消息,魏敦瑞一下子從床上蹦了起來,急匆匆地穿上衣服就奔周口店趕,結果把褲子都穿反了。
魏敦瑞的興奮勁兒還沒有過去,11月26日,賈蘭坡又發現了一個更加完整的頭蓋骨。
在隨后召開的發布會上,魏敦瑞仍難掩激動:“現在我們非常榮幸,因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發現。10月下旬曾發現猿人左下頜骨一面,并有5顆牙齒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內,又發現猿人頭骨兩具,及牙齒18枚。26日再發現一極完整的頭骨。對于這次偉大的發現,我們要感謝賈蘭坡君。”
緊接著,一個完整的人類下頜骨又在周口店被挖掘出來,和4個“北京人”頭骨化石一同送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由中美學者共同創建的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負責保管。

周口店的考古發掘成果達到最高峰之時,中國卻遭逢了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周口店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周口店發掘的“黃金時代”結束了。7月28日,北京淪陷。
此時,5個“北京人”頭骨化石(包括下頜骨)被鎖在協和醫學院解剖系辦公室的兩個保險柜內。一同存放的還有山頂洞人化石(山頂洞人距今約一萬一千年,1930年發現于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洞,1933~1934年由裴文中主持進行發掘),化石標本總計頭骨7個,下顎骨12個,還有大量的牙齒、體骨碎片等。
協和醫學院當時屬于美國,在日軍控制之外,暫時算是安全之地。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北京已在日軍鐵蹄之下,“北京人”頭骨化石隨時可能遭遇不測。
1941年,美日關系惡化,太平洋上風云日緊,在日軍占領區域內的美國機構,難保萬全。已經轉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的翁文灝對仍留在北京的“北京人”化石憂心忡忡,他從重慶給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國駐中國大使詹森分別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鑒于美日關系日趨緊張,美國正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共同抗日,我們不得不考慮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安全問題。我們準備同意將它們用船運往美國,委托某個學術研究機關,在中國抗戰期間替我們暫為保管。”
“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正是當時保存在協和醫學院的“北京人”頭蓋骨。
但是,美國人這時候卻講起了“契約精神”。當年中美聯合進行周口店科學考古的協議中,明確規定出土化石“應永久保管在中國”,美國方面據此就是不答應翁文灝的請求,雙方往來交涉,拖沓了將近一年時間。
胡頓甚至在給翁文灝的復信中說:“即便將來形勢惡化,這批標本也不可能受損,沒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損。它們沒有出售價值,最壞的情況莫過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國)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館罷了”。
這樣的說辭,恐怕只有習慣于“收藏”他國國寶的國家才說得出口,而中國,早就嘗夠了被侵略掠奪的苦果。
直到1941年11月中旬,經翁文灝的一再協調,最后又經重慶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交涉,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才給北京公使館發來電報,命令他們協助把“北京人”秘密運往美國。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這個“許可令”下得太晚了。如果美國答應轉運“北京人”能夠提早一些,哪怕只有幾天,歷史也許就能改寫。
“北京人”失蹤
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進入戰爭狀態。
12月8日清晨,日軍占領協和醫學院,立即派人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員將保險柜打開。顯然,日軍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沖著“北京人”而來。事實上,日軍早就做好了奪走“北京人”的準備。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來到北京,以科學研究的名義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兩周,協和醫學院答應了他們。事后看來,這兩周“科學研究”,更大的可能是“踩點兒”,偵察“北京人”的存放地點。
但是,占領協和醫學院的日軍還是晚了一步。他們打開保險柜,找到的只是“北京人”頭骨化石的石膏模型。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不死心,他們一方面到了周口店,自己組織挖掘,另一方面帶著憲兵,威逼當時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說出“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當時剛從法國留學歸來不久,接替離開中國的魏敦瑞,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推說自己接手不久,不知道“北京人”究竟在何處。事實上,裴文中知道轉運“北京人”的計劃,但沒有親自經手,詳細情況確實無從回答。
“北京人”離開協和醫學院是在珍珠港事件兩天前,即1941年12月5日。當時的新生代研究室技工胡承志,是最后一個見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中國人。
黃慰文介紹,胡承志是1931年進入新生代研究室做學徒工的,當時年僅14歲。他先是跟著步達生做助手,后來魏敦瑞把胡承志升為技工,參與科研并制作標本的石膏模型。上世紀70年代,已是中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的胡承志,為賈蘭坡和黃慰文講述了他見到“北京人”最后一面的情形。
據胡承志回憶,在珍珠港事變前,大約在11月中旬,新生代研究室女秘書息式白匆匆來到實驗室,要求胡承志速將“北京人”等裝好,秘密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的辦公室。
胡承志對這一天早有準備,已經做好了兩個大白木箱。兩三個月前,歸國不久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就告訴他,“‘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裝箱運走。”胡承志問什么時候裝箱,裴文中說:“聽信兒。”
現在“信兒”來了,卻不是來自裴文中。胡承志知道事關重大,當天下午先到兵馬司胡同的裴文中辦公室,向他當面求證。裴文中告訴他:“你趕緊裝吧。”
胡承志當即趕回協和醫學院實驗室,先將房門鎖上,然后開始秘密裝箱。
據胡承志回憶,兩個木箱一大一小,小的為120厘米長,30厘米高,70厘米寬;大的為130厘米長,30厘米高,70厘米寬。由于他一個人搬不動這兩只木箱,還請了協和醫院解剖科技術員吉延卿幫忙。整個裝箱過程只有他們兩個人。
胡承志將“北京人”化石從保險柜中一一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層:第一層包的是擦顯微鏡鏡頭用的細棉紙;第二層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紙;第三層包的是潔白的醫用棉花;第四層包的是醫用細紗布;第五層包的是白色粉蓮紙;第六層再用厚厚的白紙和醫用布緊緊裹住。包好后,每個頭骨裝入一個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將小木盒剩下的空間填滿,然后再將這些小木盒一一裝進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絲填實。
“北京人”化石主要裝在較大的一個木箱里,另一個較小的木箱內,則主要裝的是“山頂洞人”化石。全部裝完后,再嚴密封蓋,在外邊加鎖,并在兩個木箱的外面分別標上“CaseⅠ”和“CaseⅡ”的英文。
胡承志和吉延卿把兩個木箱搬到博文的辦公室,當面交付。他當時能夠獲知的信息,也只到當夜,這兩只木箱被悄悄運至北京的美國公使館。
按照中美協商和美國公使館的安排,這兩只箱子被標上美軍軍醫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義從前門火車站裝車,直發秦皇島,之后搭載計劃于12月11日進港的客輪“哈里遜總統號”,前往美國。
兩只木箱由專人護送,跟隨美國海軍陸戰隊登上了開赴秦皇島的專列。8日上午,列車按計劃抵達目的地。但“哈里遜總統號”卻沒能靠港。因為就在前一天,日軍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哈里遜總統號”在長江口外被日本戰艦追捕,觸礁沉沒。
而剛剛抵達秦皇島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列車和軍事人員,一夜之間就成為了日軍的俘虜。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飛。
仍未揭開的謎底
戰火紛飛的歲月,兩只裝有中國國寶的木箱,就這樣神秘地失蹤了。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樣在尋找這兩只箱子。
1942年,一個名叫錠者繁晴的日本偵探來到北京,受日本軍部委派搜尋“北京人”的下落。結果,他費盡心機找了一年,一無所獲,羞憤于“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軍的圣潔,有辱自己作為日本帝國一流偵探的聲名”,剖腹自殺。
自殺前,錠者繁晴寫了一份尋找“北京人”經過的《備忘錄》。其中記載,他審訊過裴文中、博文等相關知情人和被日軍俘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戰俘,在北京、天津、秦皇島搜查過“北京人”存放、經停的所有可能地點。可以看出,錠者繁晴已經比較完整地獲知“北京人”的轉運過程,但是仍舊沒能找到那兩只木箱。
錠者繁晴沒有找到失蹤的“北京人”,但這并不意味著排除了“北京人”落入日本手中的可能性。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作為戰勝國,中國在戰后迅速派出使團赴日本,參與受降等有關事宜,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作為使團高級顧問,負責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國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詢和找回“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裴文中為在日本的李濟提供了這些信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東京專電:“盟軍最高總部稱:前為日軍竊奪并運至東京之北京人骨骼現已發現。”(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京《英文時事新聞》載有路透社電:“東京帝國大學已將此無價之骨骼標本運赴盟軍總部。”
李濟“按圖索驥”,找到駐日美國海軍司令斯脫特。但是,斯脫特回答:盟軍司令部已經就中國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據報端的信息查問過東京帝國大學,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北京人”在東京或者在日本。
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線索,是那個名叫威廉·弗利的美軍軍醫——“北京人”出境的押運人。1941年12月8日之后,這個美國人就音信皆無。直到30年后的1971年,《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威廉·弗利的回憶文章。
文章這樣寫道:“12月8日,我在秦皇島被日軍逮捕,一周后被釋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從秦皇島戰俘營寄回的行李,以及應該裝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軍用提箱。我打開自己的行李,發現被人動過。這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兩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兩只則交給我平時最信任的兩位中國人。”
根據弗利提供的這些線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關部門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詢問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職員,沒有一個人見過所謂的箱子,甚至連知道美軍軍醫弗利的人也沒有。
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兩位朋友,專案組也找到了。兩人本是夫妻,之后勞燕分飛。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斷了來往,但兩人的敘述倒是相當吻合:弗利是托付給了他們兩個箱子,其中一箱是醫療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在不可能互相通氣的情況下,兩個人敘說一致,真實性可信,結論是:箱子里裝的根本不是“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自從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神秘丟失的那一刻起,有關頭蓋骨下落的線索就層出不窮。然而每一條線索,都在事件歷史的回溯過程中,更加撲朔迷離。
民間流傳甚廣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阿波丸”沉船里之說,現在考古學界多持否定態度。
“阿波丸”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4月在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美軍潛艦擊沉。1977年,我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打撈,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受潛水技術所限,那次打撈沒有完整結果。出水物中的偽滿洲國政要家藏小官印等物,讓人猜測“阿波丸”攜帶了大量中國北方寶物,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北京人”。
但是“阿波丸”當時是從新加坡駛向日本,如果“北京人”真的落在侵華日軍手里,他們沒有理由將其放到東南亞,也不可能直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
1980年,有人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檔案庫查到,裝有“北京人”的箱子曾存放于天津的美軍陸戰隊軍營六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這個兵營的舊址很快找到了,但是六號樓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倒塌了,之后被夷為平地改成操場。學校負責人回憶,在清理大樓廢墟時連地基都挖開了,根本沒有木板結構。
20世紀90年代,日本傳來消息,一名當年參加了侵華戰爭的老兵在彌留之際透露:“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這個老兵說他當年是日本“731”部隊的上尉軍醫,在協和醫學院進行細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軍侵占北京不久,就已經截獲了“北京人”化石,這位老兵被指定為護衛保管負責人。1945年日本戰敗后,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協和醫學院正東大約兩公里,一個有著許多松柏古樹的地方,為了日后識別,他還在一棵松樹干上,用軍刀刮下一塊長約1米、寬約20厘米的樹皮。
根據這名老兵的回憶進行勘測定位,在協和醫學院以東,只有日壇公園符合“僻靜、有許多古樹”的條件特征。而更令人興奮的是:在日壇神道北側不遠的地方,真的有一棵被刮過樹皮的松樹。中國科學院動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地表測量,居然發現那棵古松樹周圍信號“異常”。
然而,隨后的挖掘結果再次讓人失望:在古樹周圍下挖深達三米——遠遠超過了一個人倉促之間能夠挖掘的深度,沒有發現任何埋藏物。地表測量時的異常信號,其實是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所引起。
幾十年過去,每一條線索,無論可信與否都不曾被忽視,每一次都是滿懷希望,結果卻總是希望落空。在地下埋藏了幾十萬年的“北京人”,在展露面容僅僅數年后,又隱沒于時間的長河,蹤跡難覓。
時光飛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賈蘭坡去世了……幾十年中,與“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相關的人士相繼辭世。根據他們的遺愿,人們將他們安葬于周口店龍骨山上的周口店遺址內,永遠守望這片承載人類起源秘密的土地。
本文首發于《北京日報》2016年7月26日13版、16版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如遇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相關文章刊發之日起30日內與本網聯系。版權侵權聯系電話:010-85202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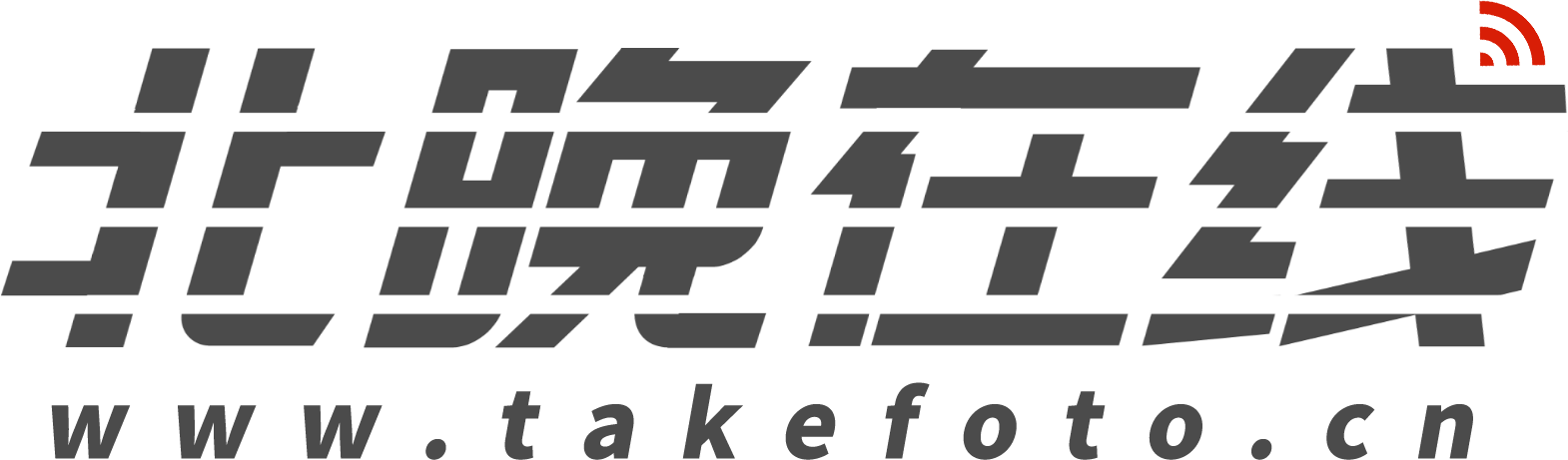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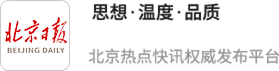





















未登錄
全部評論
0條